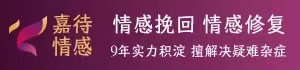斯诺登流亡这一年:在俄罗斯生活与美国差不多
小说和电影,这是普通人了解间谍最常见的渠道,其中也给我们很多可信赖的原型。比如说英国间谍都是绅士男子汉,不易屈服但比较好色;俄罗斯间谍身材矮胖,留着大胡子,出身相对低微,脸上经常有刀疤;背叛者被捕前的最后时刻多半急着焚烧材料或者是给发黄的《泰晤士报》拍照,被捕后面临残酷的测谎实验。而斯诺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过去一年,他是怎样走过来的?
中情局前局长的预言并未成真
美国前任中情局局长迈克尔·海登相信,这很可能也是斯诺登的结局。去年9月,他曾说:“斯诺登的余生要搁浅在俄罗斯———过着隔离、无聊、孤独、压抑、被酒精浸泡的生活。”
但应邀前来接受访问、在酒店房间里露面的斯诺登看上去和以上形容词全然没有联系。在逃亡到俄罗斯后的一年里,他不是被隔离,而是比以前更自由了;如果精神上感到压抑,至少不曾表现出来;而且在7个小时的对话结束后,他甚至拒绝了一杯啤酒———他说自己根本就不喝酒。
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正在筹拍一部以斯诺登为原型的电影,原想把主角包装成好像007那样彻底的英雄,但在莫斯科访问斯诺登时,他发现斯诺登根本是“非传统意义间谍”:他很安静,自我约束力极强,非常低调,谈话中使用的学术词汇级别很高。如果斯诺登有弱点———相信很多人都在寻找他的弱点———那么在以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情报员的身份泄密并逃亡后的13个月里,他很谨慎,并没有露出任何弱点。
来到莫斯科后,斯诺登还坚持按照美国时间作息,他的手表上还是美国东部时间,比一般人晚了好几个小时。起床之后他会打开3台电脑中的任意一台,这是出于安全因素,同时他还使用加密文字。对于目前的生活,他觉得和以前在美国差不多,仍和网络科技联系紧密。
他说:“我知道很多人希望我过得很惨,目前看来他们都要失望了。”
《卫报》记者艾文一年前在香港见到斯诺登的时候,他没有刮胡子,没梳头,身穿T-恤和牛仔裤。此时于莫斯科再见,31岁的他明显“物质化”很多,身穿黑色裤子,质地和做工高级的合身西装,头发梳理整齐。只是相比一年前他更加削瘦,脸色更苍白了。
他开玩笑说:“可能我离死只有三步之遥了。我吃得不多,以前总是非常忙,现在能让我专注的工作很少了。”
采访前我们不知道要去什么酒店,此前他唯一接受采访的美国媒体是NBC,那是今年5月,是在一间匿名酒店里进行的。这次他选择到我们的酒店来会面,见到熟面孔艾文时两人热情握手,毕竟一年前谁都不知道还有机会再见。
在斯诺登看来,一年中很多关于自己的报道只能说明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前同事们工作能力太低,例如嘲笑他是酒鬼或者怀疑他曾藏在玻利维亚总统的专机里。
他说:“哇,看来他们的情报糟透了,就这样还进行全天候监听?要么就是他们决定用这种方式彻底羞辱拉丁美洲国家总统和他身后代表的几千万民众。让总统专机在维也纳迫降并实行搜查实在是太糟糕了!而类似的错误还在继续,好像他们根本不想抓住我,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在政府内部有朋友!”
自己做饭购物不想成为俄罗斯人
虽然以逃亡者的身份被监视居住,但斯诺登经常自己做饭,他最喜欢日本拉面,因为最简单。他也能经常外出,他说:“我并非活在完全秘密的时空,相反我的生活很公开,我不想变成明星式人物,不想所到之处都被人关注,更不想要媒体的过分关注。”他承认自己的俄语讲得还不够好,亟待提高,因此很少用俄语在社交网站上留言,这样容易造成麻烦。媒体上偶尔会流出他的照片,一次是在莫斯科一艘游船上,一次是推着购物车在街上,他自己并不关心这些长焦模糊照片。外出是否要伪装呢?他否认自己会戴夸张的眼镜、假鼻子和假胡须,他说:“一顶棒球帽和一副墨镜就能出门,这就是我的伪装。”
他并不像报道中所指为俄罗斯某机构工作,不过短期内他不用为财政问题担心。除了之前做合同情报员的丰厚积蓄外,他也通过演讲挣了不少外快,此外他获奖很多,奖金也很慷慨。他正动议成立一个“自由媒体基金会”,希望能帮助记者们在安全条件下自由交流。
被问到在俄罗斯今后的生活,斯诺登的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他清楚自己是在监视状态下生活———同时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监视,只要行踪和日常生活不打乱,相信被骚扰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也不想成为“俄罗斯人”,一直呆在这里。和他亲近的人总说,如果想重新回到美国或者赢得美国人的心,必须更高调澄清自己的观点,斯诺登总强调人们误会了他,但具体细节却不肯说明。最近他开始尝试着交朋友而不是制造敌人,希望缓和西方观众对他的看法。
认为斯诺登是叛徒的人相信,就算他不是双面间谍,也是克里姆林宫手中“有用的白痴”。他说自己没有向俄罗斯泄密任何一份文件,他所携带的秘密俄罗斯什么都没能获得,一开始他也不想来俄罗斯,更不曾预料会在这里呆这么久,来到俄罗斯全然是因为偶然:“这是个现代化国家,而且对我很友好。”但他更期待的是能自由旅行的生活。围绕在他身边有很多阴谋论,不少人怀疑他是俄罗斯间谍,《经济学家》的专栏作家爱德华·卢卡斯更是直言,如果见到斯诺登一定拉着他去警察局。斯诺登淡淡地说:“这些说法都很疯狂,他们怀疑我在2010年9月去印度是为了会见俄罗斯情报人员或者某个中间人。其实那次旅行是因为公务,我前往美国大使馆,工作任务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编写程序。这些阴谋论不会伤害我的名誉,因为阴谋中所说的都不是我。如果真的有一丝一毫确实证据证明我是俄罗斯间谍,那么明天中午我就会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
就算不是克格勃,也有很多人指责斯诺登的泄密给西方的情报收集造成致命打击,他如何面对这样的指责?他说:“人们知道数字化交流会被监听,可是没有人因此停止数字化交流。因为唯一的选择是“要么接受风险,要么永远不进行数字化交流”。至于有人担心恐怖组织和武器扩散组织不再使用数字化通讯,这倒是个好消息,如果真因为我泄密,恐怖分子就不再使用现代通讯网络,从安全上对美国是有好处的,我们没有损失。”
也有人指责斯诺登宣称泄密是为了维护民主,但是这么做恰恰伤害了民主。英国军情6处总管约翰·索尔斯(SirJohnSawers)曾说,斯诺登这么做,导致“基地”成员们笑着摩拳擦掌。索尔斯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在去年年初,还有恐怖分子被揪出来,还有他们的通话被截查,全球范围内的情报收集工作还很成功。”———然后,就出现了斯诺登的泄密事件。
为什么不能让安全机构收集海量的、好像干草堆般的数据,然后寻找其中好像缝衣针似的有用信息呢?斯诺登不太同意“干草堆里寻找缝衣针”这样的隐喻,尽管这种说法在情报界已成为一种习惯。他说:“我觉得使用‘干草堆’是一种误导,这不是什么干草,这是人的生命意义,是人们最隐秘活动中最私人化的记录。但是这些信息被储存同时一遍一遍筛查。或许通过监视我们去的所有地方,监视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分析我们说过的每一个词汇,等待着判断结果从一个机构传到另一个机构,这么做的确能发现一个恐怖阴谋,或者发现更多的罪犯,但这样的社会难道是我们希望生活的社会吗?这就是安全国家的定义吗?”
认为现实比小说更危险更无道德
上一次读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什么时候?斯诺登承认那是相当长时间以前的事情了。《1984》是政治小说的代表作,书中讲述了一个令人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未来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描写,投射出了现实生活中极权主义的本质。
斯诺登说:“我们身处的不是好像《1984》那样的世界,我们的世界甚至更危险。因为我们能看出,奥威尔描述的所谓的‘未来科技’现在看来都弱爆了。书中还描述藏在灌木里的麦克风或者藏在电视机里的相机。现在网络摄像头随处可见,我们购买的手机都有麦克风或者录音笔的功能,时间证明今天的世界比奥威尔描述的更加危险,更加难以预料。”
但是小说里描述的在国家安全局高墙下的氛围确实与“山姆大叔”今天无所不在的监听很类似,斯诺登承认在以往任职期间,他和同事们偶尔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深刻的道德质疑。他举例说:“很多信息分析员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在18岁到22岁之间,他们突然被信任,放到重要的职位上承担重要的责任。他们突然间能接触到几乎是所有人的私人对话和私密信息,有些时候这些信息和工作没有关系,例如一个女孩给男友的全裸照片,但是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具有强大吸引力。所以他们会怎么做呢?发现照片的人把照片给其他同事看,然后某个同事会传给他的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又会传给其他朋友,很快这个女孩的裸照会被所有人看到。”
这种事情大约多久会发生一次呢?斯诺登表示大约2个月会出现一次。在没有政府机构授权、在没有任何需要的情况下泄露监控信息,这绝对是违反情报人员操守准则的,但是工作人员之间不会互相告密,而系统的内部检查,在斯诺登看来也是相对薄弱的,于是这种“失误”基本不会被发现。情报分析人员都经过严格的背景筛选,因此从某种角度说他们都是非常类似的人,一群极为相似的人在一起工作会产生超高默契,在这种默契下,每个人都清楚维护群体的秘密就等于保护了所有个体的秘密。斯诺登说:“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情报人员的一点点边际优势吧。”
难道国家安全局的内部检查真的如此薄弱吗?斯诺登认为如果什么机构出了内奸,情报部门的内奸危害将是最大的。
好像他,一个30岁的年轻人能轻易获得众多绝密情报,而且能携带这些情报离开国家安全局,最后还离开美国国境,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说明国安局内部检查的松散。毕竟这群工作人员都是地球上智商最高、最熟悉数字系统的。
不过斯诺登也强调,自己和同事们并非那些“道貌岸然的恶棍”,他们也是寻常人,就好像你和我。但是在工作中,很多人即便感觉如此做有违良知,或者对所做工作的正义性心存怀疑,他们不会抱怨,多数还是按照上级安排行事。因为国安局的历史上不是没有揭发者,而以往那些揭发者的结局并不愉快。他说:“告密的人最后都落下了‘诽谤’的罪名,他们被枪顶着背后,脱光衣服离开国安局,在家人面前赤裸,所有人都目睹过这种结局,我们都背着房屋贷款,我们都要养家糊口。”
分析者关心的是揭露人们的“元数据”
在交谈3个小时后,已经黄昏,夕阳从酒店房间的窗纱里斜射,斯诺登点了一份雪糕送到房间,放松后继续开始对话。这时,他的主题是自己和同事们都格外看重的“元数据库”。
什么是“元数据”?“元数据”就是关于我们在哪里?在网络上搜索什么?我们的联系人是谁?所有这些信息的获得不需要法院许可,但是能很大程度上揭露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斯诺登说:“对于一个情报分析人员来说,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监听到的电话对话,我们真正关心的就是元数据,因为元数据是不会撒谎的。相反,电话录音很可能撒谎,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已经卷入被调查事件或者罪案,他就会利用电话对话来撒谎,可能是使用密码语言,或者是故意透露误导信息,甚至是声东击西。反正你不能相信所听到的电话对话,但是能完全相信元数据透露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元数据是更重要的工具。”
我们开始渐渐理解,斯诺登所说的元数据其实就是“数字脚印”,在数字化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在网络世界留下自己的数字脚印,不要以为清理上网痕迹和电脑历史就万事大吉,情报人员照样能还原我们的网络轨迹。那么斯诺登如何避免留下他自己的数字脚印呢?他说他从来不会在Google或者Skype留下私人信息,也不会因为私人原因使用类似网站。不过相比政府而言,他更信任Google。他说:“跟政府捆绑是必须的,你没有选择,但是上不上Google是自愿的,你可以选择不。而且Google不会把你扔进监狱,Google也不会用无人机炸掉你的房子,如果不能确定政府的行为以及政府如何使用关于我们的数据信息,我们就不应信任这个政府。”
斯诺登同时也担心,根据他接触到的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文件,美国和英国的一些高级计算机工程师们正在努力降低互联网的基础安全性能,而这也是互联网的发明者,蒂莫西·约翰·伯纳斯·李爵士正在担心的事情。他说:“人们经常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如果在我们的通讯系统里开一个后门,那么这个后门有可能被世上任何人发现,可能是私营企业,也可能是安全调查员,有可能是大学教授,但是也有可能是犯罪组织或者外国情报机构,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是那么的负责任,那么这个情报机构也就等同于犯罪组织,现在这个政府不仅能详查你的银行账户,还能查看你在互联网上的所有交流记录。”
而政治对情报系统的失察是双重的,首先政治和情报的关系太紧密了。没有一个政治家敢于否定情报部门首脑的建议,如果后者警告他说这样做的政治后果会被视为“软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大多数的社会里,监管安全情报部门的责任就落到了最资深的政治家、或者最资深的法官肩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斯诺登看来根本没有足够的技术知识去全面了解安全工作,更不要说执行监管指责了。
斯诺登说:“去年我揭露的秘密已经说明,大家在互联网上进行不加密交流不再是安全的,所有的交流都应该被默认加密,否则具有专业保密性质的工作,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云系统、网络电话还是连线电话进行交流,都是危险的。这使得记者的工作更加艰难。记者必须非常小心他们进入的任何网络,非常小心任何连接方式,小心任何具有读卡能力的仪器,小心任何可以使用信用卡的地方,小心接电话的场所,甚至要小心电子邮件中所有联系人,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让他们掌握的非加密职业秘密泄露出去。”同样,不仅是记者,还有很多职业需要保密信息,例如律师、医生、调查人员和部分会计师,所有需要保护客户隐私和秘密的行业,都面临着新世界的新挑战。
坚信技术有办法保护使用者隐私
那么新时代科技能否与隐私共存呢?斯诺登的答案毫不犹豫是肯定的。因为他坚信技术自身能产生保护隐私的解决办法。他说:“我们在互联网传输的个人信息,应该与我们锁在日记本里的文字一样都是加密安全的,数字化信息和印刷信息不应该不同,只是美国政府,还有更多国家的政府,正让两者变得不同。”
斯诺登本人并不反对有目标的情报活动,但是他认为,对大众、多数无辜者的数字化信息随意获取和监控,无论是从哲学上、伦理上、法律上还是宪法上,都是不对的。人们是否想到在真实生活中,警察突然出现,闯进我们的房子,拿走我们的日记和照片,在我们的居住环境里安装摄像机和监听器?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不可思议的,但为什么在网络世界里,安全机构就能随意这么做?而且,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么做是有效的?
他承认,在战争期间,在调查恐怖事件期间,这种“拖网式”的情报收集或许会管用,但是现在美国没有面对战争,在本土也没有恐怖袭击发生,那么拖网式的信息收集就不再符合民主精神。安全机构辩解说这么做是为了“维护民主和稳定”,他们以为民主正处于某种威胁下,但是这种威胁是虚拟的,真正威胁民主的是他们自己。
天彻底黑了,时间过得很快,斯诺登准备离去。我们送给他一块被砸坏的平板电脑电路板作为临别礼物。这是《卫报》记者被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调查时故意砸坏的,里面记录了上一次采访斯诺登的内容,而事件恰好是一年前。
看着破坏的电路板,斯诺登惊叹说:“哇,这真是好礼物!”
然后,他半开玩笑说:“里面不会有追踪器吧?”
外面,某个角落里会有人等他,其实是监视他。他说任何时候想一个人溜回家依旧是不可能的。这个晚上会有世界杯的半决赛,是荷兰对阿根廷,我们问他会不会看,他说:“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但我不喜欢运动,我不是什么体育积极分子。”
他问我们是否愿意握手告别,我们没有犹豫伸出右手。他解释说,有关机构警告他,在合影或者握手前,必须获得他人允许,否则可能令别人陷入困境。这样说,好像他真的是个俄罗斯间谍?
他笑着说:“是的,如果你们以后想竞选公职,那么和我握过手将成为抹不掉的致命污点。”
说完,他拿起背包快速离开房间,回到他那半匿名的流放生活中,而这样的生活状态或许还要继续很长时间。
原作:卫报记者Alan Rusbridger/Ewen MacAskill
编译:潍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邮箱投递
邮箱投递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