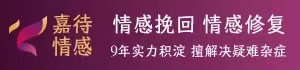火车上的30年:在超员的列车里读懂中国

授权转自看客insight(pic163)
卖淫、嫖娼、吸毒、犯罪,全在车里头,社会有啥,它就有啥。
● ● ●
在第一辆高铁驶出站台之前,火车一度是中国行进的方式。
纤细、闪亮的铁轨,从辽远而不知名的地方延伸过来,摇摇晃晃的车厢载着千差万别的人生,把那个刚松了口气的中国社会马不停蹄地发往下一个时代。
而在王福春的身体里,也有一辆不断出发的火车。容纳着混乱、肮脏与性感的车厢,令这位普通铁路职工感到兴奋。

1993年,成都至昆明,一家三口依偎入睡
车厢是个小社会,社会有啥它有啥
时间倒回至1977年。这一年,借铁路职工身份之便,王福春开始用一台海鸥相机拍摄“火车上的中国人”,三十年间从未间断。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民工潮。当时的火车车厢,是一个“打个喷嚏,钱包和孩子就会消失不见”的魔幻之地。王福春时常在车上与小偷不期而遇。
“他瞅着我,我瞅着他,他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

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被乘警铐起来的小偷,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他盯着镜头,有点窘迫和茫然。
车上的偷儿会斯文地把自己的西服挂在邻座的皮包上,等着下车时顺手牵羊。
而王福春却掩饰不住兴奋,一上车就来回窜,眼睛四处乱看,也不落座。“这30年在火车里头,我就像个职业小偷。只不过他们偷的是钱,我偷的是影像。”
第一趟先找感觉,发现故事就摁快门。走到第三、四个来回时,人家就烦他了。十分钟后,乘警来到王福春面前,要查他证件。

1991年,从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一位抱着孩子的父亲警觉地盯着镜头,不知眼中压着的是怒是惧。
在车上的三十年不是白白过去的——除了被当成小偷、被警察查证件之外,这期间还发生过许多事情,大部分都被他定格在黑白底片里。
“吸毒的,扎了那么大的疤。有些大款在车里做这做那,我都拍过。”

1997年,从哈尔滨开往济南的列车上,一名吸烟的乘客。
上车“搞春运”之前,值乘过上百万公里的老列车长召来一帮列车员,语重心长地训话说:“我们站的地面,是大社会。等下上了车,就进入小社会。小社会,出了事更难办,大家要留个心。”
车开了以后,就什么都有了。“卖淫、嫖娼、吸毒、犯法,全在里头,社会有啥它有啥。”——还有一不留神把孩子生在火车上的。
1980年的一天,列车上的广播响了:找医生,有人要生孩子。车上果然有好几个医务人员。而王福春也拎着相机跑过去,但被列车员拿布和窗帘挡了回来,说男的不让。

1997年,从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新晋父母正入神地凝视着新生儿。
虽然拍摄时常遭遇障碍,但列车上的事情总归逃不过他的眼睛,包括“列车员是怎么回事”。
80、90年代,列车员爱“带熟人”,一趟车超员100%到200%是常有的事。
在这样的车厢里,5米比外面的500米还要漫长。有时候,硬座车厢的人们,端着印有“康帅富”字样的泡面碗,经历半小时的厮杀才接到的一杯热水。

从1983年起,春运成为“全国性的大交通”。由于旅客众多,停靠时间又短,乘务员会帮忙将旅客“塞”上列车。
● ● ●
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有过三次乘火车的大潮,王福春都见证过。
头一次是1966年的“大串联潮”。从四面八方坐火车上京接受检阅的红卫兵见车就上,一律“免票”。所有的车次都没了发车时刻,人一装满就开。
第二次是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潮”,前后持续了三、五年。每到停站的空隙,知青们就下车,有人戏说,这是监牢里的人出来“放风”。

当时的窗户是可以打开的,经停站点的时候,乘客可以下车,吸口烟或者买点当地的特产解馋。
八十年代,“春运”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新经济政策打破了“圈地为牢”的旧体制,中国农民像出山的虎,涌到有工可做、有钱可赚的富庶之地去。
火车成了民工潮的最明晰的见证。浪潮所及,全国没有一条铁路轻松。

1995年7月,从武汉开往南宁的一趟超员列车上,门头角落里,一个五六岁小女孩光着膀子,满身汗泥,站着睡着了。
面对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物种迁徙”,当时的绿皮火车远远无法满足其运力需求。
铁路部门于是将货车当作客车之用,所谓的“棚代客”列车应运而生。

从南宁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当年一位年轻的妈妈对如厕不便的发明。
棚车里头没有座椅,也没有厕所,只有少数带有铁窗。整个车厢倒是像一个闷罐,白天闷热如同汗蒸,夜里则是天然的冰箱。
用竹席围挡而成的“厕所”,因空气不流通而臭味熏天,仿佛车里装的不是人。

1995年,在武汉到长沙的地段,车外高温38.9度,车里干脆就40几度的高温。一位民工没有座位,光着膀子躺在座席背上休息,为了不掉下来,他不得不抓住上面的行李架。
既然水远山长,何不来圈麻将
虽无立锥之地,但火车上最不缺的,就是随遇而安的民间智慧。

1994年,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为打发时间,乘客们组了一桌临时牌局。说笑中输输赢赢,不觉得半天过去,车又穿过一个省。
王福春常常在车上听到这样的对话:“还有五六个小时呢,要不玩会牌吧?”对面扑哧扑哧吃着面的人迅速喝完最后一口面汤,说:“好啊!”
“老哥来一起玩吧 , 两个人没意思。”
随后第三个人也加入其中,牌局很快就开始了。
不爱交际的那位,则窝在一旁,静观对局,车窗凹槽里塞满了他无声的烟头。

1996年,从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中铺女青年拉起了二胡,她的自娱自乐吸引了上铺和下铺的关注。

1999年,从北京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上,卧铺车厢的过道里站满了做广播体操的人。
南腔北调,鼻息相闻,火车就像一系列“特别关系”的集合。
那时,长途列车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姑娘坐在你旁边,她困极了,就下意识地靠在你肩膀上睡着了。你虽然也困,但为了陌生的姑娘能睡好,一天一夜纹丝未动,等姑娘醒了,马上决定要嫁给你。

1994年,北京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一对情侣站在过道里默然对晤。

1994年,从北京开往沈阳的列车上,相互依偎的情侣。
至于落实到现实里,周云蓬曾在《绿皮火车》中写过:
一个姑娘在我旁边坐下,很有方向性地叹着气,我心里窃喜,莫非传说已久的艳遇来了?
我问她是否遇到什么困难。她说老板拖欠工资,现在身无分文,要回家。我连忙拿出卖唱时别人塞到我包里的饼干、面包,与她分享。
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去青海湖的火车。我问她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她说,她有男友了,既然你都把话说明了,两人再一起走就太尴尬了。
她要去兰州,我只好去格尔木了。我想最后拥抱她一下……但上车时人很挤,她一把把我推上车,车门就 ‘咣当’一声关上了。”

1997年,在哈尔滨开往齐齐哈尔的途中,一名男青年向对座的乘客展示新婚的结婚照。
如果遇上40小时以上的长途路程,遇到的故事就更宽广了。
他留意过火车上的对话:斜对面讲的是一大串不足凭信的、在乡下听来的下流事情。后一排是传销现场,讲成功,金钱,治国平天下。耳朵感到腻烦了,再换个台。9点钟方向,一个姑娘正谈着她那个即将见面的男朋友,她为他买了一桶红玫瑰,不料塑料桶漏了,淌了一车厢的水。也有漫无目的的青年,背着吉他,任意地登上一趟不知去向的列车,向素味平生的人吐露心声……
当然,如果邻座是个时刻酝酿着吐痰的赤膊大汉,那么你将什么也听不见,除了他频率极高的喉部扩张声。

1998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一位92岁的老方丈,戴着洁白的手套为女青年号脉。

1995年,西宁至郑州,妻子为丈夫按摩。

1999年,北京开往广州的列车上,一位刚割了双眼皮的女乘客揽镜自照。

1992年,从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开往古莲的列车上,各自占了一张长椅睡觉的男女青年。
至于那些买不到(起)坐卧票的,就放下矜持,打着赤膊坐在过道上睡觉,时不时发出令人侧目的呼噜声。直到上厕所的人从他身上跨来跨去、推着小车的列车员把他弄醒。
那个时代的列车推销员,卖零食用的是对联式的4A级文案,上联“啤酒饮料矿泉水”,下联“瓜子花生八宝粥”,横批“来,腿收一下。”
等小推车的聒噪声变远了,又再躺下。别着头蜷着腿,安忍如大地。

装满盒饭的小推车,未必能慰藉饥肠辘辘的硬座车厢。上来卖方便面和西瓜的小站村民,给了封闭的车厢另一种选择。

1995年,从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在宠物狗旁吃方便面的女青年。
瑟缩在同一条过道而缔结的友谊、共饮一瓶啤酒所带来的热络、分享小桌板的默契,在车厢里比比皆是。
运气好的话,遇上不同省份的旅伴,还可以从广州吃到漠河。

1999年,从香港九龙开往上海的列车上,卧铺车厢内手捧哈达的年轻喇嘛,他们来自甘南拉卜楞寺。

从兰州到北京的列车上,两位回民在做礼拜,神情虔敬。
当速度成为主角
在王福春开始“拍火车”的1977年,国民经济复苏,铁路上跑的十有三四是“采购员”。到了80年代,走南闯北的“个体户”和“推销员”开始一统列车。90年代中期开始,富起来的中国人也热衷于去旅游。
就这样,不同时代、宗教、职业的人物直接或间接地蓄积在他的镜头里。
而在随后的十年,变化陡然加剧。

1986年,18次特快列车从哈尔滨开往北京。这一年,电视机第一次悬挂在这趟车的车厢里。当时,电视机在百姓家中还很少见,全车厢的人都伸脖子看电视。
1993年,《人民日报》报道:“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将有旅客10亿人次需要输送”,当时我国总人口不到12亿。
速度与卫生成了中国铁路的当务之急。

1994年,从沈阳开往大连的列车上,当年的“大款”用“大哥大”通话。那是当时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于是,1997年发生了两件值得记忆的事。
这一年的春运,铁路开始取消“以棚代客”的做法。中国铁路也开始了第一次提速,最高运行时速达到140公里。

1999年,从哈尔滨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一桌乘客插着耳机收看微型电视。
及至2007年4月18号,中国铁路迎来第六次大提速。次年,动车组首次投入到春运大潮之中。
很快,王福春上车拍照,电视挂在头顶上,却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乘客们仿佛一夜之间持重了许多,都低着头在网上冲浪。
“买我皮带,传宗接代”的广告文案也与时俱进,改成了“手机有电,感情在线。”列车推销员卯足了劲地喊:“充电宝啦,有没有人要充电宝啊?”

1996年,从北京开往呼和浩特的列车上,因空调太冷,硬座的乘客用椅套当成被子。
2018年2月1日凌晨,随着第一辆列车驶出,为期40天的春运正式开始。
春运第三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880万人次,其中高铁是主力。

1995年,经停小站的列车上,一名买土特产的乘客。这样的景象如今已基本绝迹。
而在王福春的眼里,蒸汽机车则像一头喘着粗气的庞然巨物,徘徊在21世纪的门口,说“要不我就不进去了吧”。直到2005年12月9日,王福春把它拍到退出历史舞台。
● ● ●
南下北上,东去西往的三十年里,王福春累积了一万多张底片。2001年,他先后卖了三台机器,出版了《火车上的中国人》。
那个黑白如薄雾样的年代,终于跃然纸上。

在丹麦展览时,一位荷兰摄影师在久久凝视一幅作品。“他说,这张照片我买了,一张什么照片呢,就是一对情侣躺在一个被窝里头(那张)。”王福春对记者说。
画面里,姑娘眉如柳叶,鬓挽乌云,正深情地望着小伙子。那是一个晨光初醒后的故事。火车穿过漆黑的隧道,他们开始亲吻。有几个隧道特别长,他们就能亲上三五分钟。
王福春问他为什么是这张,对方回答说:“中国人含蓄,情感不外露。这张就是中国啊。”

1996年,广州开往成都的列车上,挤在一个下铺上的情侣。
那天,他们下了车,卧铺上留下了两个空白,如同一块历史的空隙。
只有它知道,那两双年轻的眼睛里,为何会同时闪烁着希望与迷茫。
- END -

MORE | 你错过的精彩内容
毒舌科技 l ID:dushekeji
长 按 二 维 码 , 一 键 关 注

推荐毒舌科技的好朋友"创业邦",ID:ichuangyebang
商务合作请加微信:bangbuluo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 1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7904742
- 2 日本又发生6.6级地震 7807851
- 3 王毅:台湾地位已被“七重锁定” 7713696
- 4 全国首艘氢电拖轮作业亮点多 7617966
- 5 中国游客遇日本地震:连滚带爬躲厕所 7521182
- 6 日本震中突发大火 民众开车逃命 7426548
- 7 男子带老婆买糖葫芦被认成父女 7329843
- 8 日本地震致多人受伤 超10万人需避难 7231709
- 9 高速公路上一车龟速占道引众怒 7136916
- 10 “人造太阳”何以照进现实 7044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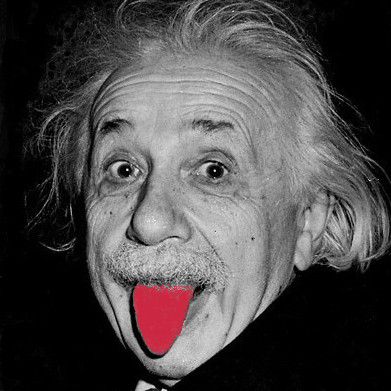 毒舌科技
毒舌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