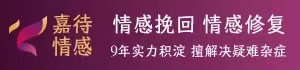盒装人生
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刚刚落下帷幕,这是9月23日10强决赛选手的24小时战作品之一——选手们两个选手一组(两人采写同一个人),在早上8点抽到采写任务,然后找资料、采访,第二天早上8点前交稿。24小时战是为了考察选手的现场写作能力。
以下为选手原文,未作任何改动。
文 | 王呈伟
周末的北京城,哪里不是游人如织的?或许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走近它便仿佛走近了无尽的荒凉。
从地铁八宝山站出来,沿着石景山路走300米后左拐,右手边便是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白色的墙、黛青的瓦砖沿着上庄东街向上攀爬,左手边便有一些殡葬用品店。其中一家,挂着蓝灰色的招牌,上面写着Ennhome、银灰,骨灰盒平价直营店。

厂与梦
En是英语词缀“使之……”的意思,而home是“家”的意思。“我做的就是为去世的人提供一个家。”——这便是银灰的老板、骨灰盒设计师张烛远在《超级演说家》上的开场白。
1984年的初春,还在做医生的张浩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一个男婴呱呱而落来到了他身边,他给这个孩子这样一个名字:烛远。洞幽烛远,他希望他的孩子不必似骄阳赛烈火,只需要做一只燃烛,尽己所能照得更远。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清雅的名字终成了父子间同一份事业的谶语。
四年后,张浩开设了一个玉器厂,唤之“雅芳”,为殡仪馆提供骨灰盒批发服务。那一年4岁的张烛远在父亲的厂子里抱着一包包榫子玩,长桌子两端个摆一个,是两个堡垒。他不知道这些是什么、要被做成什么,他也不知道他的未来将会贴着榫卯相切的每一条缝隙成长。
小小的张烛远在厂子里慢慢长大,渐渐地会向父亲和前辈们提出自己的想法:例如设计之初的设想、雏形出来之后的修改,甚至产品卖出之后的建议。在他深爱的姥爷被装进这样的盒子之前,他对于盒子依旧没有概念。
生活依旧继续着,张浩和“雅芳”在2004年向前迈了一大步。那一年,我国殡葬行业部分地向市场放开,民营资本逐渐走入,张浩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为自己的骨灰盒厂取名为“银龙”,却意外被登记错,成了“银灰”。这阴差阳错之间,倒成就了“银灰”这样一种颜色,一种张烛远称之为“让阴暗的色彩变得更光明”的颜色。
张烛远作出这种解读时,他已经33岁了,这一年距离他接管父亲张浩的生意已有9年余。而9年前,让他接管家族生意的那件契机,他依然记得深刻。
2008年,张烛远的母亲被诊出癌症,曾经的工作狂张浩顿悟生命的无常,于是将生意抛给儿子,携起妻子的手便带着她四处去旅行。但是那一年,设计骨灰盒既不是张烛远最想要做的事情,也更称不上是自己喜爱的事业。
张烛远在大学里学包装工程专业,课余生活中是外联部的活跃分子。他享受将事情全盘规划好并一步一步实施的过程,活跃在每一个能表现自己的舞台之上。
直到今天,他依旧会遗憾:做策划则会有更大的舞台,而骨灰盒设计总归是受众太小了。
但是,从业9年之后的2017年,他登上了《超级演说家》的舞台,将自己在店中的所见所闻一一描绘出来,打湿人眼眶。他在演讲开始前,还骄傲地说过:我是一名骨灰盒设计师。
节目播出的那一天,他发了条朋友圈:十年圆梦。
那一刻,两个走上分叉路上的张烛远在路口再次相遇了,这一次,他们相视一笑、握手言和。

父与子
“我对我父亲的评价是……负、正、负、正,到现在的正负交织。”
在外人眼里,张浩是个文质彬彬的人,他儒雅到能给一家玉器厂取名“雅芳”。但是张烛远眼中的父亲却是掌握了绝对权力的霸主。在他还小的时候,张浩总是打他。况且张浩忙于事业,经常不在家,年幼的张烛远反而与姥姥、姥爷更为亲密。
张烛远回忆起父亲缺位的童年时,说起母亲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但他现在的古井无波,却依然被归于父亲的打压式教育。
即使父亲成功的事业也曾让张烛远钦佩不已,但是他的霸权父制再一次让青春期的张烛远感到失望——他甚至不让张烛远穿帽衫,因为那不是正经孩子的打扮。
父亲眼里正经孩子什么样?张烛远至今不知道,他只记得那一年他去剃头,剃头匠说:“我给你理个板寸吧,只收你普通理发的钱。你去学校有人说好看,你就帮我宣传宣传。”张烛远觉得自己既省了钱,理发匠又赚了吆喝,这是个双赢的结果,便答应了。
可是当张烛远顶着板寸头回到家时,迎来的却是张浩的一顿臭骂,原因还是那一个:这不是一个正经孩子该有的发型。
直到接手父亲的生意,曾经刁难过父亲的艰辛与压力被自己扛起时,他开始理解那份苦,学会了尊重。
但这种和解只是表面的,他和父亲依旧相互读不懂。直接表现在对店面装修的分歧之上。
张烛远坚持认为店面的环境会直接影响到家属的心情,应当重新装修店面。但张浩却觉得认为产品的质量是唯一的标准。
于是16年年初,张烛远趁着父母外出游玩的时间,赶紧找来装修团队,一把将图纸塞给了他们。
装修队看完图纸,给了个期限:“30天。”
张烛远算了算日子:“不行,我父亲15天后就回来了,必须在他回来之前完成。”于是装修队加班加点,赶在张浩回来之前完工了。装修的成本确实很高,但是张烛远认为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情”——给家属的舒服是无价的。
“怎么成这样了?”张浩回来看到店里的情况,很吃惊。但是他没有像张烛远意料的那样大发雷霆,他只是说:“你觉得要这样做,就去做吧。”
大概,张烛远猜测,父亲这么多年终究还是有所松动的;或者是因为他们都还在一句话上能够保持些一致:宁可做错,不能不做。
张浩很高兴他们之间关系能够缓和。但他不清楚,自己的儿子依然承受了一些来源于他,又与他没关系的压力。
2008年,张烛远代替张浩去上海参加殡葬展会。这一行的圈子很小,小到一个同行发现张烛远很面生后便当面问他:“你是谁,之前没有见过你。”
张烛远说:“我是银灰的。”
“你和张老师什么关系?”
“我在他家挺久的了。”
“不可能!我跟张老师很熟的。你是新来的吧。”
后来,张烛远坦白了自己的身份,那位同行瞬间堆起了笑脸:“啊呀!张浩的儿子呀!”
那一年,张烛远24岁,带着刚入行的冲劲和狂妄,却在这里被冲刷得一干二净。张烛远不明白:我有名字啊!你为什么不看我名牌上的名字,只看到了我的父亲?
在父亲的巨大阴影之下,张烛远被套上了一层枷锁,而且随着时间的增加,越捆越紧。
在张烛远看来,圈子里的所有人似乎都在盯着他:“哦,你是张浩的儿子啊。那你做的好是天经地义的,料在你手里,好工在你手里,那个团队在你手里,你要是这样还做不好,是不是太脆了?”
但当你真的做不好时,别人就更开心了:“看吧,你就是不行。”
张浩是自己的父亲的这个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张烛远否认自己是父亲的学生,他说:“如果你全跟着他学,你就只能做一个50%的他。”张烛远在不断地寻找出路:他读书,读明代家具设计,也读现代的创作理念;看日本也看世界,他说他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天花板,想要效仿日本那家开在银座的骨灰盒店,去打破那种制约。
张烛远在寻觅的这条走出行业瓶颈的道路,或许也是他走出父亲的阴影的方法。
但是,他又会迷路,行到水穷之处后不得不承认:父亲在这方面(设计骨灰盒)其实要比我强的多得多。

故事与设计
张烛远依然忘记不了自己第一次独立设计的作品,那是2011年,距离他接手生意已经过去3年了。那一天,一位七旬老翁找到张烛远,想为自己的父亲换一只盒子。他拿来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说:“我想把这个刻上去!”张烛远仔细一看,原来这位老翁的父亲生前是一位老革命,纸上写着的全是他参加过的战役。
老翁坐下,说:“盒子要大方,但不要显得太空……带雕刻但是不能多。”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想法,张烛远听老翁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却抓不住什么重点,于是连蒙带猜做出了他的第一版:一个方形盒子,上檐带了倒角,表面留白以供刻字,托底做了些砖刻。
老翁来看了很久,一直皱着眉头,向下用力地瘪着嘴,喉咙里发出几句咕噜声。张烛远知道老人家不满意,便坐下来继续听他絮叨。断断续续地,老人家讲了许多父亲生前骁勇善战的故事,语气中满是掩藏不住的自豪。
张烛远听着他说,不停地猜测他的念头。老人家说着说着也急了,质问:“你看我都说得那么细了,你怎么还是不能明白呢?”
张烛远这时却已经猜出来了,老人家要的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庄严肃穆。他想要一种霸气、一种与众不同,就像他父亲的生活一样。
于是第二稿出来了,整个骨灰盒分三大部分:棺、椁、托。行内有句话:内为棺外为椁。椁是棺外面的罩子,罩在底托之上,中间被罩的棺就是真正放骨灰的盒子。
这个版本的设计做了大变动,椁的上边刻着一圈回字纹,取家庭吉祥和睦之意;中间是一个相口,用来放相片,边上带了点麦穗。
里面的棺为了呼应椁,也在上半部分做回字纹;下边则将战役的地点画一个圈,连成一片,就像北斗七星一样。
老人家很满意,即使他说不上来哪里满意,就像他之前不明白自己哪里不满意一样。唯一有缺憾的是瓷像,老人家总觉得父亲的这张照片显不出其高大伟岸的形象。张烛远便提醒他:“这里也不一定非得放相片的。您的父亲生前喜欢什么吗?”
老翁立马回答:“他喜欢写毛笔字,家里都收着呢,一张也没丢。”
“伯伯您看,您这个盒子整体已经很大气了,在相口这里不如加点温馨的东西吧。”
后来他们在老先生的书法作品里找到了一个精致漂亮的草书:“家”。
最后的成品效果很好,老翁满意地不停向张烛远点头:“谢谢小张,谢谢小张!”
时隔六年张烛远再回忆起这件事时,依旧觉得很舒服。他认为设计和演讲都是一样的:“不是你想说啥就说啥,也不是观众想听啥你将啥,而是你把观众想听的说出来。设计盒子就是这样。”
他想来想去,觉得好多事都是这样的道理:想让别人感激,得首先自己享受这个过程。就像是为妻子设计小浪漫小惊喜时一样,得自己想着想着就能先乐出来。

死亡与浪漫
死亡是任何一家骨灰盒店里都不变的主题,而张烛远最大的身份转变不是从一个策划变到一名商人,而是由一个表达者转变成一个倾听者。
某天,一位阿姨进门坐下,张烛远递来的水没喝一口,便开口了:“我们家老头是xxxx年参加革命……之前我们在上海工作,又搬来了北京……我们家原来住在大院子里,后来又分下来一套房子……前两天我们还在打麻将……”
店里还有一位客人,五年前的7月17日,她来店里为女儿置办了一件骨灰盒,就是已经获过奖的那件《百花丛中》。于是每年到了那个日子,她便会来店里再坐一会儿,聊一聊家常,说昨天又跟闺女说话啦……
张烛远冷静地分析这些手足无措的顾客,他像个智者一般为他们递去擦泪的纸巾。他可以客观地总结出到店的三类顾客,也会给大家科普亲人去世后三个容易出状况的时间点。
但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在失去至亲这件事上,感同身受是个伪命题,除非你同时或者曾经感同身受。”母亲的病和姥爷的过世,是张烛远所有直面死亡的经历中最惊慌的两次。
如今,9年过去了,母亲的病早已经渡过危险期,有父亲专心陪伴她游玩在每一个城市里,她的脸色甚至比得病之前更红润了。张烛远也早已回归平静的心情,似乎又变回了那个温柔的倾听者。
但张烛远还是有所不同了,他叨叨着一句老话好多回:“天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说来说去,还是这句:“珍惜眼前人”。
“父母喜欢玩,但也不带我了。”他顽皮地提起了父母,话锋一转便又提起他的妻子。
张烛远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两人是相亲认识的。结婚七八年了,别人总和他提七年之痒,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确实痒啊,她一年有175个夜班,我见不到我的媳妇儿,我心里痒啊!”
因为妻子经常要值夜班,他们便有一场“24分钟的恋爱”。在妻子的两个夜班之间,有24分钟的休息时间。这不到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妻子本可以不回家,但她一定会回来——这样,张烛远牵着她的手将她一路送到医院门口。48小时之内,这24分钟是唯一的相处。
张烛远看着妻子的背影,心里抱怨着她怎么不回头看看自己,又忍不住目送她走进医院大楼才离开。他有时候也会想,会不会突然有一辆车从黑暗中冲出来……
话说到一半,张烛远不说了,他做了个鬼脸:“这样好像在咒她啊,不好不好。”
想她的时候,张烛远就发个小表情给她,也不期待她的及时回复,只是告诉她“我想她了”。
在他的演讲最后,张烛远用力地说道:“从现在开始,放下那些无谓的追求,抓住此时此刻能抓住的最重要的东西。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每一天,真正地活过。”
他说着“真正地活过”,背起了一句诗: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10强选手参赛作品集
完

内容产业报道第一媒体
微博 @刺猬公社
合作、转载事宜请联系微信号yunlugong
投稿邮箱ciweigongshe@126.com
网站www.ciweigongshe.net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7904747
- 2 紧急提醒:请在日中国公民进行登记 7807897
- 3 中央定调明年继续“国补” 7714002
- 4 “九天”无人机成功首飞 7617307
- 5 断崖式降温!今冬最强寒潮来了 7523004
- 6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信号:3件事不做 7428104
- 7 中国“空中航母”首飞成功 7329412
- 8 中央定调明年货币政策 7233547
- 9 人民空军中日双语发文:大惊小怪 7138904
- 10 寒潮来袭 “速冻”模式如何应对 7043388










 刺猬公社
刺猬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