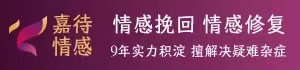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不会满足于现状,也不愿随波逐流,不会轻易找到一把‘椅子’坐下。”本文来源 “投中网”(ID:China-Venture),腾讯创业经授权后转载。
周炜并不掩饰自己的矛盾。
作为昔日硅谷老牌基金首批成功的中国管理人,周炜对自己的投资手笔十分自信,不论KPCB时期,还是创办创世伙伴CCV之后,他自认做到了现有条件的最好——35%的独角兽命中率,6年便将基金DPI做到1——如果你对当下基金普遍业绩有所了解,便知这已是不低水准。
矛盾源于更大的野心。周炜目前的焦虑是,CCV成立6年,虽然已经投出4个IPO和8个独角兽,但尚无一个所谓“超级案例”傍身。如何在普遍遇冷的周期,再次投出像京东那样的代表作,重回超一线的领跑者,这是周炜定义的“再次跑赢”。
风险投资市场是个信息不对称的行业,基金的真实业绩往往并不易得,外界对基金的认知很自然就落在了那些高知名度的“代表作”上。在烈火烹油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那些抓住机遇与超级案例实现深度绑定的基金,可以吃到最大的投资回报,也收获了几乎一劳永逸的市场名望。而剩余玩家,难免暗淡一些。
再战跑赢的机会还存在吗?不知道。但周炜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位置,也依旧坚守着自KPCB时期承袭下来的投资审美。对于当下的状态,他这样描述:不会满足于现状,也不愿随波逐流,不会轻易找到一把‘椅子’坐下。
毕竟,矛盾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主持人: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学习积极分子,投资圈隐形KOL
嘉宾:周炜,创世伙伴资本(CCV)创始主管合伙人,不肯找“椅子”坐下的投资人
杨晓磊:你之前公开提到一句话,宏观变化不是摆烂的理由,这是对自己说的吗?周炜:可以这么理解。春节到4月底这段时间,美元基金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很焦虑,每天找很多人谈,试图想清楚未来到底什么样子。4月底我想明白了,既然环境这样,无非就是判断还能不能干,能干,环境对谁的影响都一样,就不是需要考虑的变量,在决策和思考体系就要剔除。其他没什么意义,不然就成祥林嫂了。周炜:对。这个时代中国市场的某些条件甚至比移动互联网时期还好。只要不被打断,中国的“机甲时代”一定会到来。杨晓磊:问题捋清楚以后,你在投资和管理层面做了哪些调整?周炜:我们基金是团队作战,前五年一直是温和友善的环境,现在更强调精英文化,针对有成绩的人给机会。现在大家面对的是场“完美风暴”,需要每个人都是最好的。周炜:有点像一个电影情节,一面激光大过滤器网格正向我们迎面移来。只有两类机构能突破:一种是巨大无比的,有不同资产类别,能量护盾大到把过滤器撞破;另一种是尖尖的锥子,某个打法有专长,可以直接从网格中间穿过去。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变成尖锐的锥子。杨晓磊:我们常给基金做尽调,发现美元基金的业绩普遍没有想象中优质,一方面,可能跟赛道转换有关,移动互联网这类过去高速增长的赛道不再,另一方面,这跟打法有关系吗?美元基金到底应该坚持一贯打法,还是应该更像本土派,广撒种子,追求更强的确定性?周炜:美元基金过去十几年的打法是对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数学算法。大多数人民币基金不是纯粹的VC打法,更像PE打法,所以我认为这是PE和VC打法的区别。不过千万不要认为VC的商业模式“放之四海皆准”并能持之以恒。VC模式有点像桃花水母,只能在非常干净的水里才能生存。周炜:VC的商业模式相对脆弱,只能存在于生态环境非常好,创业、创新这些要素都存在的情况。这些年VC太热了,以至于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全宇宙存在的东西,其实不是。VC成规模的存在超过20年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和美国还有半个以色列,其余市场基本消亡了。日韩基本都是CVC。欧洲也很难找到纯粹的VC。中国过去20年高速成长,VC获得高回报是正常的,但当市场进入另一种状况,那就不一样了。周炜:2005年真是个大年,大量外资机构进入中国,本土品牌密集成长,一批特牛的创业者做出了特别好的东西。另一个好年份,2008年到2009年,所谓“金融危机”时期。2011到2012年也是大年。一大批成熟的创业者再次出发,成功率很高。今年呢?我本来认为是个好年份,因为好项目可以用合理估值投,但这两年又有个特有趣的现象,泡沫已经让估值透支好几年,估值只能上不能下,比较尴尬。周炜:拉平去投。某个年份集中投资,我认为是一种投机。假设基金的投资周期是3年,投资就应该均等在这几年,这才是对抗风险的方式,所以我们有portfolio的概念。周炜:一直都很平均,一年二十个左右。人民币基金正常投资,美元基金今年有些压力,适合投的项目没那么多。但我们最近发现,海外华人有一些不错的创业项目,我们叫中国企业家的溢出效应。周炜:只要大格局不波动,我认为是通的。中国的产品出海是最容易的,产品链条完整,人机交互做到很好,交付即可用。现在的中国有些像七十年代的日本,如果没有外部干扰,应该会有大量中国企业爆发式的往海外冲,发展出一大批世界级企业。相对而言,我更看好中国企业家直接在异国创业,而不是在中国做了企业再出去。中国的创业环境,用《三体》的说法叫“黑暗森林”,这种环境出来的企业家,在纯粹能力上明显比海外企业家强一些。杨晓磊:元宇宙呢?美元基金都在布局,但它到底是大平台,还是眼下美元基金没什么可做,但应该去关注的题材?周炜:很多人把元宇宙和Web 3.0等同。起初可以划等号,但现在大家谈的Web 3.0,我认为只是浮在元宇宙上的一些应用。简单的说,我赞同元宇宙是下一个类似互联网的大平台,Web 3.0只是其中类似支付宝这类应用层的东西,算是元宇宙的一个重要环节。元宇宙本身非常有价值,问题是一群人混进来,借这个名做别的事。但那是元宇宙有问题吗?不是。Web 3.0技术本身是个好东西,但也有很多人把它当作炒币的工具,自然就产生了问题。另外,这些东西还在初期,真正有价值的并不多。换句话说,现在跟九几年互联网刚出现时一样,很多泡沫。周炜:我们目前看的方向介于2和3之间,看一些所谓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安全、审计和通用技术等等,但还没有在所谓的核心圈子出手,那里应用层的东西太多了,跟我的观念相悖。周炜:我是创业者出身,有一个持续增长的价值对我最重要,但Web 3.0大部分应用目前看不到场景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如果投资人很难等到真实价值产生后分利润的那天,就得想办法立刻变现。Web 3.0是要求快速变现的,对于我们这样的投资机构,底层逻辑和组织结构不能支撑这种快进快出。VC做投资,安排退出一般是一年后甚至更长周期。但在Web3.0,动不动就是个把小时,应用层也迟迟看不到真实场景和价值累加,这是主要矛盾。但我还是坚信,无论到Web几,持续创造价值的模式总归有价值,我们也坚持在自己的能力圈范围内做投资。如果尝试一段时间,发现不是我们能handle的,也不是什么致命问题。专注自己擅长的就已经足够好了。杨晓磊:元宇宙的故事天天在讲,但有一点我抓不到准,元宇宙到底是消费层的东西,还是能渗透到产业的东西?你是科幻爱好者,你的看法是什么?周炜:方向绝不只是2C,我们刚投了一家2B的工业数字孪生。所谓的元宇宙,我们2016年就开始投,一共投了10个项目,当年元宇宙这词还没出来,我们叫数字孪生。从 PokemonGO游戏开始,我们有个认定,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可以通过某种技术链接起来,或者叫人机交互。真正的元宇宙时代,做产品时就要考虑数字孪生和IT的结合。举个例子,设计一台发动机,一开始就把所有设计过程和部件数字化、孪生化,如果后面出现故障,可能戴个AR眼镜就能指导你找到问题,像玩游戏一样,但凡会装宜家家具,玩乐高的人,都能在指导下完成最复杂的东西。再往后就是向Web 3.0里介入。再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工程师,遇到一个问题,你想出解决方案并且修好了,就可以把这个方案上传到软件平台。未来有人遇到类似问题,系统会自动告诉他,这个问题有人解决过,你付1000元就能用他的方法解决。如果这套软件能做出来,可以想象,很可能会诞生出中国的数字孪生版本的“达索”,放海外也会摧枯拉朽,因为它是真正下一代的产品。中国有很多后发优势,我很看好。只是现在扎实做事的人不多,发币太赚钱了,再好的人入了币圈都很难不被诱惑。杨晓磊:我们今年的投中峰会上,商汤徐立提了一个概念,说未来的元宇宙时代,AI技术已经完善,可以支持元宇宙各种场景,元宇宙流通的大量内容将不是由人创造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容尤其经典内容,都是人写的。按照上述预测,难道不会有伦理层面的挑战吗?周炜:这是个好问题。刘慈欣有本超短篇小说《无法共存的节日》或许可以回答。一九五几年的苏联,加加林飞入太空,一个外星观察者假扮的基地工人向总设计师表达庆祝。工人说,其实真正值得纪念的节日你们都没有庆祝,比如细胞第一次分裂,海生动物第一次爬上陆地,而不是圣诞节什么的。总设计师来了兴趣,问,那今天算什么节日?工人说,分娩节,人类一直是个胚胎,没有离开过地球,今天第一次离开子宫(地球),婴儿诞生了,所以是分娩节。两人对话结束以后,外星人发了一条信息给总部,说今天正式进入他们定义的分娩节。另一个故事,二零五几年,脑机接口成功,人类可以通过脑机直接跟机器交流,主设计师很兴奋,说要庆祝,这时这个外星观察者假扮的工作人员说这也是个节日,值得命名。叫什么呢?流产节,意思是有了这个东西,人类就可以简单廉价的活在虚拟世界,满足自己一切的要求,虽然没有消亡,但也没有向外探索的必要了。对话结束之后,外星人又发了条信息,要求删除分娩节,因为有了流产节,人类不可能离开地球去探索宇宙了,只会在“子宫”里死掉。周炜:有启发,但是有人可能悲观过度了。很简单,人类历史上,真正有强烈探索精神的开拓者有几个人?中国有张骞,西方可能会多一些,比如哥伦布。这放人口里是极小的比例,也不需要那么多人探索,所以不会因为有个元宇宙,这些人都不想探索了。换句话说,理工科人什么特征?当一个技术已经在这了,但你不可能停止把玩的欲望,就像小孩面前放了玩具。假如伦理问题考虑过多,那么今天这一切技术都没法发展了。杨晓磊:今天又变回科学家的时代了,技术人才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时代积累到了出成果的时候?还是外部因素带来的?周炜:对科学家的推崇,肯定是中国的局部特征。大国必须有大国科技策略,政策推动起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时机也到了。时机很重要。我是学物理电子的,按专业背景来说,我懂芯片,但我也不认为比如二十年前是投芯片的好时机,当时整个产业链条缺失的环节比较多。移动互联网的代码可以天马行空,但科技硬件比如芯片、材料,都是实打实的“科学通货”,没有通货再怎么搞也出不来。周炜:经历了20年的软件时代,现在其实硬件发展落后于软件。刚说的元宇宙,已经有在卖五维座椅配VR眼镜了,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追求完美体验。但方案还远不完善,大量硬件跟不上。硬件复兴是必然。大国策略下,芯片等硬科技底层必须成功。我的结论是,如果一个产业链条,大部分节点都是我们领先,浮现巨型企业是必然,移动互联网也是同理。我投出了京东,但也经常讲,这些巨型企业出现是必然,出在谁手上是其次,链条决定一切。举个例子,机器人制造的大部分节点中国都领先,AI至少跟美国平行,自动驾驶技术全世界最好,几个技术结合在一起可以想象出未来所有的智能机器人,中国的机甲时代快来了。杨晓磊:现在抢项目这么卷,机构又大量上规模,中小机构怎么抢筹码?周炜:LP也会问这个问题。我不是巨型基金,不需要吃掉一切,拿到5%就可以。换句话说,只要投对两三个方向,基金的回报就足够好。还有个模式我们一直坚持,同一个模式的公司,我们只投一家,不会投竞争对手。一个初创VC品牌,要在市场赢得创始人的认可,专业是一个角度,成熟的创业者最终也会知道要合作的人是谁,投资不是单纯放一笔钱进去。周炜:我们只拿历史业绩说话。但你说得对,LP会问一样的问题,我还是会告诉他们,只要赢得局部,就能带来超额回报,不需要在全局。周炜:KPCB时期,我负责的两支基金,科技投资部分虽然只有两亿美金额度,但回报都超过10倍,百倍以上项目有6个。成绩可以说无以伦比,我也非常自豪。现在最大的焦虑是,创办新基金之后,怎么再跑赢?现在肯定不算。周炜:至少是大家公认的,能在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早期科技基金,做不到我认为就是输了。具体来说,不但每只基金都要高回报,而且要有超级案例,这才算是赢。周炜:我们有明确方法论,每年投出一个独角兽,每支基金回报至少实现5倍以上,但好像在市场看来,这远远比不上多年不收获,第十年跑出一个超级独角兽。这是VC一个特有现象:有那种明星案例在手,一定会被认定是超级牛的投资机构。只是基金业绩稳定,永远不会被认为是最牛的。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了,想被认定为超一线,你得有那个超级项目,它能持续产生磁吸效应,像一块磁石持续吸引新的优质项目。否则人家只觉得你是一个还不错的新基金,你只能靠自己不停辛苦去挖掘,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们始终在追求那个未来的超级项目,持续高回报加上超级项目,才能实现良性循环。杨晓磊:团队是焦虑的原因吗?我之前问过一个机构配置,上面一群合伙人,下面没几个投资经理。我说你这不对,一般都是金字塔式。对方说,放那么多合伙人就是为了抢案子,需要什么人就直接挖。包括一些头部机构也是,挖人的pay非常高。你们怎么搭团队和培养?周炜:投资机构有两种,金字塔是一种,另一种完全不要中间,几个有业绩的人一起做。各有利弊,选了“金字塔”就必须把规模做起来。CCV承袭了一些KPCB的理念,专注早期,投项目希望占比10%以上,一定有董事会席位,投了项目绝不只是跟随,而是要积极参与进去,每个模式只投资一个项目,集中资源支持创业者。团队我也倾向自己培养,carry分配要到位。每一支好基金基本是一个人贡献95%,不管这个人是小咖还是大咖,要保证做出成绩的人拿到的分配至少相当于一个重要GP能拿到的。VC做了这么多年,没有见过carry的很多。杨晓磊:99%吧。一朋友刚从某VC离职,机构开出特别苛刻的条款,比如说三年不能加入其他VC,不然之前案子全没,想拿到carry更是没可能,除非放弃过去的经验不干了。周炜:很多都是这样,目的可能是留人。问题是,市场那么多基金,禁止得过来吗?周炜:策略、打法、团队几个方面基本没有变化。2009年后,KPCB对中国的介入只在投委会投资决策层面,但日常运营包括招人我们是独立的。2010年初我开始负责基金的TMT投资,完全就是独立基金的模式,投资策略也是我们定。从结果来看,在当时非常有限的资金配置和受制于全球投委会的决策模式下,我认为已经做到那个环境下的最好,所以现在还施行一样的东西。周炜:投资决策更高效了。以前是全球投委会,但大部分投委会成员不懂中国,也没有接触过这类项目。如果靠看文件和有限的讨论做决策,容易出现无效情况。现在我们投委都要集体去见项目,而且要把行业前三五名的公司全见一遍,横向对比。所以我们合伙人工作量很大,比一般机构累很多。杨晓磊:有没有这种可能,方法越沉淀,越难投出大案子?过去一些超级案例,我认为纯粹是撞大运。周炜:敢不敢冒险,和有没有系统的方法论,我认为并不互斥。我们主要投早期,大部分项目投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之前有个项目就拿手机做个demo给我们看,我们也投了。投的时候估值才一千万美金,后来最高估值时候40亿美金,账面回报400倍,马上也要上市。周炜:我们有个逻辑,如果一个人不懂某个方向,但有投票权,建议他就不要过度参与决策。所谓的民主,如果每个人说话都一样重视,这是错的。出现了分歧,一般交给花时间最多、最专业的人去做判断。但这种策略只是保底,VC从来没有苦劳,要么赚要么亏。周炜:一看运气,二看有没有人敢坚持。可能前面都错了,第三次对了,回报就是巨大的。我尊重这种坚持,基金要允许有人在非常自信的时候冒险,问题或许就能突破。杨晓磊:自2017年成立至今,最大的单笔投资是多少?周炜:数坤放了1亿多人民币,占整个人民币基金近10%。对我们来说相对大了。我们不是那种一个项目放百分之二三十资金的机构。杨晓磊:等上市的过程中,LP会给你们施压吗?现在LP对DPI都挺焦虑的。周炜:施压谈不上。我们人民币基金一期目前的DPI预测非常好,十月刚刚完成一个IPO,另外有三个项目即将上市。不出意外的话,光数坤一个项目就能完成一倍以上的基金回报。但确实感受得到LP期待尽快,尤其这两年。杨晓磊:这几个案子行业差异很大,有元宇宙还有医疗,投的时候判断方法一致吗?周炜:大逻辑一致,但每个赛道不同。最重要的是分析赛道和模式的不同特征,再去匹配团队的不同能力,一个赛道尽可能投入足够多的人进去看透。周炜:很简单,一个好创业者应该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比如最成功的创业者绝不仅仅是为赚钱,他有那种抑制不住做大事的冲动。杨晓磊:之前听过一个类似说法,企业家要自带愤怒感。但这事也有个挑战,如果不长期跟踪,你怎么判断这个火苗还在?周炜:这就是早期投资艺术的部分,跟对方坐这交流一小时,就要有个结论。表演一个小时的火苗也没那么容易。杨晓磊:有句话圈里常说,做企业能做出作品,但做投资很难,你怎么看?周炜:我也一直是这么说。VC在这个作品里的功劳太小了。这行为什么会被神化?因为不管中国早期还是美国早期,一些创新的想法没人给钱,所以才有所谓“没有伯乐,千里马就埋没”的说法。但今天只要是个项目都能拿到钱,多少的问题。伯乐的概念不存在了,那VC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多少有一点,但VC仍然只是驾驶员身旁的人,提醒下个岔路口左拐或者右拐。最好的VC可以做好驾驶员的导航卫星。周炜:考虑过,比如要不要孵化一个公司。只是做投资以后心态变了,看事情都成了战略性视角。如果能找到特别牛的团队做可以,但真要自己挽起袖子干,我想绝大部分投资人干不成。投资人每天看新东西,有时跟创业者聊15分钟就不耐烦了,有人说投资人不尊重创业者,但有些东西投资人已经听了5年、10年,还有人一直在讲,投资人也要耐心听下去。周炜:强迫自己喝茶,尤其遇到重要事项,我一般捧一杯茶跟人谈。有了泡茶过程,人就不会那么急。杨晓磊:募资也是个精细活,给美元LP和人民币LP得讲不同的故事吧?周炜:美元融资的特征,是同一套话你要讲100遍,人民币融资的特征,是每个LP你都要针对特征讲一个最新的的认知。杨晓磊:KPCB当初在中国那么水土不服,你为什么还待了整整十年?我相信中间有过其他选择。
周炜:我其实辞过三次。第一年就提过,当时太波动了,北京团队就剩下我一人,连办公室都没了。第二次是京东的C轮,连着被毙掉两次。你问为什么留下?可以说KPCB的品牌占很大成分,我前十一年创业虽然挺成功,但内心里还没达到理想的高度。我上沃顿时,没什么人知道我以前的公司,即便我参与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曾经是国内特别牛的公司,但却比不过别人拿着贝恩、BCG的名片,人家马上就过来谈。KPCB的平台能给到的资源确实太好了。在美国,每次想见谁,只要发出邀请,对方马上同意见面,而且是一对一。同事都是John Doerr,Mary Meeker,Al Gore 这种级别的人,当时中国大部分项目都是模仿美国的,我通过KPCB能看到很多国内看不到的前瞻性的东西。杨晓磊:这十年时间,对你作为一个投资人最大塑造是什么?周炜:影响非常深。KPCB是一家秉持正统投资理念的VC,也是一家有理想的基金。我们也希望这样,所以我们打造的团队做事风格非常正统,绝不走歪门邪道,不然肯定待不长久。但是过于过度情怀也不行。KPCB过早投资了绿色科技,这一理想化的决策太超前于时代了。但凡晚个十年,就有很高回报。不过说实话,刚才聊天,你说看到我一些挣扎,你看得挺准的。我的挣扎在于,VC是个职业角色,作为受托人必须给LP赚钱,有carry也不至于富到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也有一些非常想干但可能回报一般的事。很多机构在投航空航天,我也想投,但不想投只是把老技术重做一遍的公司,我想投真正有革命性的东西。杨晓磊:你是创业者出身,把企业做到上市又卖掉,然后去了读沃顿MBA,再后来是投资人,现在又回归到投资人+创业者各一半的角色。回头来看,哪个选择你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周炜:这个问题很有趣。无论是作为创业者还是投资人,每个阶段都会享受不同的角色,没有哪段经历是没有价值的。比如做了投资之后,我发现创业经验对于我理解公司成长有非常大的帮助。其实我们这代人,很多决定不是自己做的。我高考报考四川的大学,只是因为父亲希望能落户回家,没什么深思熟虑。后来创业也一样,不是我做的决定,是社会帮我做的。周炜:大三时打网球时认识了几个创业的年轻人,很偶然就参与了他们的创业公司,设计出了中国第一代POS机。那时只要6000元一台,比进口的30000元便宜太多,公司很快占领了大量市场,实现爆炸式增长。当时我们十几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在外面租了个宿舍,一起吃饭喝酒做公司,我还配了个大哥大,太快乐了。那时还是国家分配工作的年代,主流是去国营单位,各种研究所,我不喜欢那种一成不变的工作,毕业就留在这家公司,这是我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也是主动抉择。第二个重要选择是卖了我创立的第二家公司,去美国念沃顿商学院。那家公司是银联的第三大大技术合作伙伴,一年利润很高,但是2005年我卖掉了,所有人都很震惊。周炜:卖掉肯定是财务的巨大损失。换今天的见识,我可能安排个特牛的CEO帮忙看着,再想办法上市,一举两得。但从看世界的角度来说,我不后悔。我在KPCB和沃顿看到的东西,一起工作的人,简单来说,让我可以从此不再仰视任何人。读完沃顿后,我深知顶级商学院的好处在于,你身边这帮人将来是最牛的,跟他们一起工作你会产生一种平常心,因为你发现没有超人,也没有天才。他们的成功,一是大势,二是专注。这给了我非常强的信心,不论天分,只要够专注,就能成功。周炜:我没有天分,唯一的长板就是专注努力,心无旁鹜。我人生这一路,从求学到工作包括在沃顿商学院,不管哪个平台,我很快就是跑得最快的那个,没有输过。包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每天就想着把事情做到最好,没想太多回报的事。当然,那家公司也特别好,完全以结果论英雄。我毕业半年就当上分公司总经理,毕业三年就当上大区总经理。有个事特逗,那时还在KPCB,有次和一位创业时期的老同事见面,见面第一句话对方就说,周炜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他说当年我在公司新加入的应届毕业生中像神话一样,感觉下一轮CEO非我莫属,结果现在拎个包,每天给创业公司去投点钱?我当时很吃惊,我在全球最有名的投资机构,他为什么这么说我?杨晓磊:你说不管在哪,你都能成为跑得最快的人,但凡事有两面,有时跑得太快,可能看不清方向。投资讲究时机,KPCB进中国比后来所谓的vintage year晚了两年,CCV也比VC 2.0的2015年晚了两年成立。你觉得自己在大势把握上有钝感吗?周炜:我们投的项目很多都是“第一股”,从这点来看肯定没有。但你问有没有钝感?可能有。我做事的风格有点像郭靖,要把一套拳打扎实,而且我认同巴菲特的一个理念,创造价值是永恒的。投资这件事,我要做的是什么?最好的时候,我们或许不是顶点,但最差的时候也能保持该有的收益。杨晓磊:这套理念放到今天的市场环境,会不会很难自洽?投资做减法,只追求局部赢,不担心把自己路走窄了吗?周炜:非常好的问题。什么是自洽?其实就是选把椅子坐。椅子就代表一个成型的理论,选一把跟你理念接近的椅子坐下,从此你就舒服了,身边一堆人是你的战友,你会觉得非常安全。到目前为止,我的矛盾在于不甘心全盘接受,也不甘心随波逐流,所以没法选择一把椅子坐下。我最大的理想是做出一支成功的基金,有多个团队,每个团队都有很牛的领导,我给他们充分空间去施展策略,只要理念一致,战略合拍,业绩优秀,我就不干涉。周炜:一个组织能基业长青,必须时时刻刻有新鲜思路注入肌体。能突破重重风浪到达彼岸的,一定是一支舰队,而不是一艘船。舰队中每条船各司其职,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所以对我而言,最终的自洽可能是我给船长们提供了什么价值,有了价值,船长才会在舰队各自管理自己的船只。我面临的是个人突破的问题。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腾讯创业
腾讯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