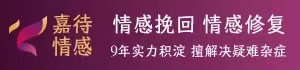癌症刚治好,一种罕见疾病让他的肺“变成了石头”

图片来源:Pixabay
可能是由于化疗带来的副作用,一位患者在癌症缓解后,患上了另一种致命但鲜为人知的疾病。
撰文 | Richard B. Woodward
翻译 | 张逸飞
审校 | clefable
如果医生的诊断没错,到了明年这个时候,我大概已经死了。而我将因为一种鲜为人知的、致命疾病——特发性肺纤维化而死。
肺医学领域的临床医生迈克尔·斯蒂芬(Michael J. Stephen)2021年出版的书籍(Breath Taking:What Our Lungs Teach Us about Our Origins, Ourselves, and Our Future)中,将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描述为一种“在肺医学中最令人绝望的疾病”。在很短时间内(确诊IPF后,存活时间的中位数是3年),患者囊状的肺泡中就会充斥着粘液,且会不断硬化。由于肺部无法再行使关键的功能——向血液供氧,患者的呼吸会变得越来越急促和困难。用斯蒂芬的话说就是,肺“变成了石头”。
然而,这种疾病鲜为人知的程度和其在人体内的发展速度一样令人震惊。美国每年大约有4万人死于这种疾病,比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数要多5000,仅比乳腺癌少一点。斯蒂芬估计美国每年有20万人在IPF的阴影下挣扎求生。但是,IPF并不像其它疾病,有电视广告、公路赛、彩旗或者冰桶挑战之类的活动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募捐治疗的费用。
2年前,当我被告知患上IPF时,我完全没有听过这种疾病,而我所有的朋友也都没有听说过。当时最让我担心的其实是结肠癌。2019年11月,我经历了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医生将我的大肠中一块硕大的肿瘤切掉了。除此之外,癌细胞还扩散到了我身体中的多个淋巴结。

结肠癌|维基百科
所幸癌症并没有扩散到我身体的其它部位,按照医学标准,我被诊断为癌症三期(癌症处于中晚期):病情严重但仍可以通过治疗缓解。从2020年初开始,我接受了12个疗程的化疗,随后的结肠镜检查和验血显示,我体内已经没有了癌细胞的踪迹。
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在好消息的背后,在6个月的化疗中,我所使用的强效药物除了帮我克服了癌症,也带来了一种罕见的、此前已有记录的副作用。
在化疗结束后,我拜访了我的肿瘤医生,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化疗可能会带来这种副作用。我原本以为,这次见面将是我们战胜癌症的一次庆祝。但当时,他指着一张我胸部的CT片告诉我,上面出现了瘢痕迹象,或者说我出现了“玻璃肺”。(在放射学影像中,受损的肺组织会显示为白点或者是不透明,表示那里的肺泡被堵住了)他建议我去找一名肺科专家看看。

IPF患者的胸片,出现了网状结节性混浊。|维基百科
起初,我并没有特别担心。“玻璃肺”听起来并不可怕。我想着这种疾病可能就像支气管炎(bronchitis),用上一剂抗生素就能治好,完全没有想过这些瘢痕可能意味着我患上了某种致命疾病。毕竟,它又不是癌症。
直到19世纪,医生们才开始了解肺纤维化,但一直没有什么办法缓解相关的症状,而关于这种疾病成因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好像没有人了解患病原因。医生们确认我患上了IPF,但无法确定是否是由化疗造成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显著延长IPF患者的寿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在2014年批准了尼达尼布(Ofev)和吡非尼酮(Esbriet)这两种药物上市,因为临床试验显示它们能减缓肺部恶化的速度。我每天需要服用两次尼达尼布,每次两个胶囊。而一瓶尼达尼布(含有60个胶囊)的售价就高达一万美元,好在一项医疗补助金帮我缓解了部分经济上的压力。
我并不知道这些药片有没有发挥效果,而我的医生似乎也不清楚。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IPF没有治愈的可能性,且一旦发病就不可能停止。正如我第一个肺科医生所言,这种疾病“无药可救”。
在这种疾病的各种症状向我袭来之前,没有任何预警。2021年5月,我还能每周3次进行两局网球双打,而2个月以后,仅仅挥一下球拍,我就会气喘吁吁。医生给我开了类固醇吸入器以及大剂量的泼尼松(prednisone),最开始几周,它们还能够减轻我呼吸困难的症状,随后就没用了。

图片来源:Pixabay
如今,我在长岛的家中已经布满了又细又长的塑料管,它们将我和呼吸机连接起来。呼吸机每分钟可以产生10升氧气,而我需要连在两台呼吸机的其中一台上,每分钟吸入6升氧气,一天24小时都如此。出门时,我会带上一台便携式呼吸机,虽然它的功率没有那么强大,但可以允许我进行一些自由活动。同时,我也会尽量避免去一些太远的地方,因为一旦离开呼吸机太久,我的血氧水平就会严重下降。
作为一名艺术评论家,观看展览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不过,当我要去博物馆时,只能坐在轮椅上让别人推着我——我已经没有力气推自己了。我感染过一次新冠,症状很轻。如果再感染一次,且症状更严重的话,我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我已经69岁了,对我来说,要想活到70多岁,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肺移植。但像我这样的患者目前已被禁止进行肺移植手术。在美国大约有65家医院可以进行肺移植,但患者必须满足五年内没有患过癌症这一条件。如果有奇迹发生,我能再活3年,那我还需要最少2年的时间才能等到可以单侧肺移植,而想要一个完整的肺则需要再等3年。等到那个时候,我已经75岁了,超出了有资格进行肺移植的最大年龄限制。我到时也会死去。
在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后,我改掉了自己拖延的习惯,就像像俄国文学里那些得了肺结核的人物一样,在精神和行为上得到了解放。但事实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的变化。我那本已经拖了很久的、关于摄影与暴力的书,还没有任何进展;按计划本应开始的纪录片项目仍然遥遥无期。现在,除了关心每天的健康情况之外,思考任何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讽刺的是,本来应该救我一命的化疗药物,可能就是最终杀死我的东西。对此,我不知道是应该感到可笑还是愤怒。
或许,IPF不受关注正是因为在治疗方法上的探索,仍然举步维艰。当科学家们对某种疾病有了新的认知时,记者们通常会蜂拥来进行报道,而在IPF这个领域,一直都没有一些能带来希望的前沿性消息。相比之下,前列腺癌和肺癌等疾病的治疗进展及相关的报道上,就显得乐观得多。
对于医生来说,当知道没什么治疗方法能让患者活下去时,自然也就很难鼓舞他们振作起来。尼达尼布也只能减缓我的肺不断“石化”的速度,但最终结局还是无法避免。
就像斯蒂芬所说的那样,IPF是“肺科疾病中最大的谜团,这个疾病如此神秘,似乎人类难以逾越”。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医疗机构能尝试去破解IPF的秘密。这种疾病也迫切需要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站出来,为它募集更多的研究资金。只有更多人意识到了这种病的存在,庞大的医疗产业才会研究强有力的技术,着手去解决这个难题。
作者介绍:Richard B. Woodward是美国纽约的一名艺术评论家。
参考链接:https://www.statnews.com/2022/09/05/dying-of-idiopathic-pulmonary-fibrosis-a-disease-i-never-knew-existed/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环球科学(ID:huanqiukexue),如需二次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 1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7904716
- 2 贪污超11亿!白天辉被执行死刑 7808170
- 3 王毅:是可忍孰不可忍 7712363
- 4 全国首艘氢电拖轮作业亮点多 7618469
- 5 河北沧州杀妻案男方被判死刑 7522506
- 6 水银体温计将于2026年禁产 7426436
- 7 日本强震 高市早苗神色慌张一路小跑 7334110
- 8 日本地震致多人受伤 超10万人需避难 7236734
- 9 《大明王朝1566》逆袭成国产剧天花板 7142615
- 10 “人造太阳”何以照进现实 7048681



![徐紫茵 情人节快乐 是时候发这组寡淡风照片了[草泥马]](https://imgs.knowsafe.com:8087/img/aideep/2022/6/8/514434b383950a3cda9711a91308c445.jpg?w=250)



 果壳
果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