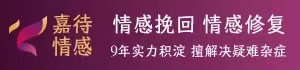青少年网络霸凌: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折断了别人的伞
在网络霸凌后,少女直播跳楼
7月26日,网名依奈的18岁少女直播跳楼自杀,直播最后的画面定格在了夏季晴朗湛蓝的天空。

在直播跳楼之前,依奈就曾被确诊为抑郁症,并多次尝试自杀。
两年前依奈在一款名为康帕斯的游戏中,将自己的ID改为“拿不到金头就自杀”。金头是游戏排名前10的玩家奖励,在赛季结束时,依奈的排名没能使她拿到金头。
根据朋友转述,她真的准备履行“诺言”自杀,但最终被朋友劝了回来。
今年4月,“康帕斯隔空喊话bot”举办了一场活动,活动中使用的角色恰好是依奈特别喜欢的角色,因此她加入了相关的QQ匿名群。
入群后,群里有成员认出了她,然后向“隔空喊话bot”供稿,嘲讽她说要自杀却不自杀,随后多条以“金头姐”为黑称的投稿在该微博上被发布。
依奈在QQ空间、微博等处尝试反制这种攻击,并多次与对方沟通,但对方仍持续在微博评论区中辱骂依奈,
在北青深一度对此事件的调查文章中写到,“依奈的网友阿吉猜测,依奈遭遇持续网暴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她多次自杀未遂,‘他们认为她是装的抑郁症。’”
直到7月26号,辱骂攻击都未曾停止,即使依奈直播间里只剩下一片蓝天,相关匿名群聊中还是没把它当成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

依奈自杀后相关匿名群中的言论 | 《匿名网暴,无处可逃:“魔法少女”依奈生命的最后三个月 | 深度报道》@北青深一度
随着依奈的确认死亡,网暴者们并没有反思或是道歉,而是开始抱团与推卸责任:

微博@敬畏生死-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施暴者与依奈是同辈人,有些人年龄比依奈还小,只是高中生甚至初中生。
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需要负责的事务让他们分心,在校园之外,手机上小小的屏幕塑造了他们生活的底色。
而在互联网的角落,对生活感到痛苦、失望与不满的青少年并不少,在抱团之后,他们将自己宣泄情绪的根据地命名为“网络厕所”,它可能是小众贴吧、隔空喊话bot,或是匿名QQ群。
当生活中积蓄的负面情绪指向具体存在的个人时,网暴就此发生,而依奈事件只是所有网暴的冰山一角。

另一位遭受隔空喊话bot形式霸凌的用户
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会越过底线,在网络上做出这种霸凌行为而不自知?这可能与线上去抑制化效应有关。
线上的我,好像是另一个人
无论网速多快、体验多拟真,线上人们的行为始终和线下真人互动不一样:比起线下,人们对自己在线上的言行更不加以控制。这种偏差被称作线上去抑制化效应(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1]。
这个效应的理论基础是,人们在线下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是处在一种 “抑制”的状态中,因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我们会逐渐学会去抑制一些当下看起来不太合适的行为,例如我们会学会隐藏情绪,不会暴露自己太多的脆弱,更不会暴露自己的攻击性。
但是在线上,这种抑制化现象会被削弱:在线上,我们会和陌生人分享最私密的事情、最脆弱的情绪,也会把最恶毒、最凶狠的一面释放出来[2]。
去抑制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人们在线上可能表现得比线下更有同情心、更乐于助人,这被称为“良性(benign)线上去抑制化”,像是匿名树洞中人们会更愿意说出自己的故事并得到他人支持,多人线上扮演游戏中的“工会”组织里的情谊经常让人感到温暖等[3]。
研究表明,在社交网络上自我表露可以提高幸福感,减轻社交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线去抑制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自我表露的正面效果更加显著,这就是一种良性的线上去抑制化[4]。
另一方面,“有害(toxic)线上去抑制化”现象也不可忽视,人们同样会出现在网络上对自己的恶意和恶行更不加以控制的情况[5]。

目前有关青少年网络去抑制化效应的研究,基本都聚焦在有害线上去抑制化现象上。例如针对2407名中国青少年的问卷调查显示,对交往不良同伴较多、共情能力较低的青少年而言,其线上去抑制的观念越强,网络霸凌行为就会越多[6,7]。
去抑制化后,
人们为何会释放极端的恶意?
线上交流的几个特征,使得人们会更肆无忌惮地在去抑制化后更加极端地攻击别人[8]。
首先是匿名性(anonymity)带来的“无责任感”和“安全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抑制性,通常是为了保全我们的社会身份。不管是完全隐去ID的匿名,还是频繁更换的小号,在我们的概念中,它们都不能代表作为社会人的我们。
随时启用、弃用一个账号时,我们就可以卸下社会身份这个抑制我们的枷锁,在现实的网暴事件中,事情闹大后改名、换马甲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

一些对厕妹行为的评论 | 半次元
二是缺乏反馈,缺少共情。当青少年面对面与人交流时,能够看到对方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表现出喜悦或受伤,这种反馈会影响到青少年接下来的行为,使他们更加积极或是收敛。
但在线上的文字交流中,青少年看不到对方的表情。这种不可见性(invisibility)使得人们无法及时收到这样的反馈,因此失去了对自己言行的约束。
无法与被攻击者面对面,会让口吐恶言的人们低估自己言行的严重性。
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攻击并非打在一个实在的人身上,而是打向了一个“虚拟”的形象,这就使得他们的攻击更加不加节制。
异步性(asynchronicity)进一步导致了缺乏反馈。除了实时聊天软件,线上的很多交流形式并不是同步的,人们不是在实时互动,不必实时接受对方的反馈,甚至可以说完就跑,一击脱离,这种现象被心理治疗师卡莉·门罗称为“情绪的肇事逃逸”(emotional hit and run)。

线上交流反馈的不足,导致线上交流成为一种“唯我论内部投射”(solipsistic introjection),换句话说就是自己脑补:在我们阅读别人的线上文字的时候,我们会对这场交流进行很多脑补,比如脑补对方的声音、性格、文字后面的深意等等。
这种脑补,通常是我们自己与自己进行的交流,比如依奈事件中的网暴者自行认定她是富人,然后自顾自地说自己讨厌她是因为仇富;又径自认定她是在无病呻吟,明明身心健康,有这么多人支持,却还是每天悲伤,简直是不可理喻。
他们将自己生活中的不满全都化为言语的利箭,投射在了依奈这个具体的人身上。
当人们并不是真的理解了对方的感受与观点,而是在自说自话、对着想象中的那个“对方”自言自语时,真的很容易说出恶劣而过分的话。
最后一点,就是离解想象(dissociative imagination),进一步带来了“无责任感”:有人会认为互联网就是一场游戏,他们在互联网上做的任何事情都和他本人没有关系,线上和线下的他们是互相离解的,因此这就更加导致了人们对自己线上言行的不负责。
霸凌者需要被惩罚,更需要接受辅导
惩罚当然是必要的。
2012年,加拿大发生过类似的事件,15岁的中学女生阿曼达·托德(Amanda Todd)在YouTube上发布自己被网络跟踪、欺凌与骚扰的“沉默控诉”影片的一个月后自杀,网络霸凌由此立法,成为警方可能认定的犯罪。

阿曼达的视频:他们说希望我看到这个然后自杀
即使如此,网络霸凌依然在网络世界层出不穷,多次出现,并且形式不断翻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跳舞,而由于网络的特殊性,很多霸凌其实是难以被察觉的。
例如曾在Tiktok上流行的“GUESS WHO”视频,就是掩饰为游戏的一种霸凌:被霸凌者的身体部位与侮辱性的身份相关线索被组合成了一个短视频,比如“蓝眼睛”、“爱讲坏话”、“每周都换男友”、“平胸没屁股”的描述加上霸凌者的鞋子与后脑勺,然后让视频作者会让观众“猜猜这是谁”,并鼓励他们在评论区写下被霸凌者的名字。
这种霸凌不同于直接的言语攻击,很难被追责,但对受害者的打击一点也不小,“网络霸凌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地与受害者如影随形。地点更不限于学校、购物中心,甚至能够受害者的家中──过去在这些地方,通常可以避免传统形式的霸凌。”
而霸凌之所以会长时间持续,并不是因为霸凌者不懂事,而是霸凌者已经将自己的霸凌行为合理化。
在依奈亲友发布的微博中,有这么一段话:

微博@敬畏生死
不理解这里提到的“价值观”,就无法理解青少年网络霸凌的源头。
校园霸凌的相关研究中有一个理论:霸凌并不是不懂事的打闹,而是一种对社会规则建立的模仿,是建立权力与地位的社会化行为。
因此,霸凌者往往有一套自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网络厕所用户对自己行为的辩解
同样的,网络暴力也往往有个看似正义的理由。在一项样本为1219人的调查中,对“大学生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微博暴力行为”这一问题中,选择“事件当事人行为恶劣,为社会不齿”为第一位的人最多,为41.09%,其次是选择“他人攻击侮辱自己,无法忍受”为第一位的人,占比34.57%[9]。
对于青少年霸凌者而言,“你的表现为我们小团体所不齿”,“你的行为碰到了我们这群人的红线,是对我们的侮辱”,就能成为攻击对方的理由,而这些小团体的红线,被青春期的“悲惨”遭遇给扭曲了。
台湾学者邱献辉总结了七项霸凌行为的心理需求,其中一点就是宣泄与爆发,比如长期受欺凌后心理受创,没有适当宣泄管道转而欺凌更弱小者,或是无力回应现实环境的压力,转而将霸凌作为发泄压力的渠道[10]。
这其实就是一种自私行为的传递:个体在遭遇他人自私对待后,也倾向于自私地对待无辜他人[11]。
在厕所用户攻击他人的投稿中,表达自己“有过心理疾病、曾被霸凌、穷、惨”等元素的内容其实相当多。

某条厕圈投稿
依奈跳楼之后,网暴者声嘶力竭喊出的“凭什么”,看似是“凭什么她能得到社会的关注与同情?”,其实是“凭什么我就得不到爱?”
霸凌行为的背后常隐含着憎恨、偏见、无知和恐惧,将霸凌视为宣泄爆发的人,看似张牙舞爪、戾气十足,实则内心相当脆弱。因此邱献辉写道:“对他们如果只是惩处、没辅导,能解决问题吗?”
根据中国学者2013年的统计,至少有34.84%的青少年承认曾经在网上霸凌过别人,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12]。
由于其隐蔽性、广泛性以及难以追责性,面对青少年网络霸凌,我们除了惩罚已经造成悲剧的加害者外,更要关注青少年群体心理状态,这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共同警醒。
青少年们需要学的第一点就是,把对方当人看,当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看。
要看见,对面是个活生生的人
无论在网络上宣泄负面情绪的需求有多强烈,最重要的底线是,宣泄负面情绪的对象不应是一个具体的人。
研究发现,缺乏眼神接触是有害去抑制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其影响甚至大于匿名性,也就是说,当线上互动中加入“对视”这个动作后,人们有害的去抑制化行为就会减少[13]。
现实生活当然不能顺着网线和对方“对视”,但人们可以把屏幕后面与你对话的那个人,真的当做一个实实在在、会痛会流泪的人。
依奈去世后,她的QQ空间背景仍然使用着游戏角色“超绝可爱天使酱”的一张截图,截图里超天酱面带忧郁地说,“如果大家能少说几句比较过分的话就好了。”

希望大家都能“看到”屏幕后面那双悲伤的眼睛,少说一点过分的话。
参考文献
[1]Cheung, C. M., Wong, R. Y. M., & Chan, T. K. (2016). Online disinhibition: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 to aggressive behaviors.
[2]Antoniadou, N., Kokkinos, C. M., & Markos, A. (2019). Psychopathic traits and social anxiety in cyber-space: A context-depend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laining online disinhibi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9, 228-234.
[3]Lapidot-Lefler, N., & Barak, A. (2015). The benign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Could situational factors induce self-disclosure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9(2).
[4]Chan, T. K. (2021). Does self-disclosur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enhance well-being? The role of social anxiety, online disinhibition,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organisations and societies: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from AI to technostress (pp. 175-202).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5]Wachs, S., & Wright, M. F. (2018). Associations between bystanders and perpetrators of online hat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oxic online disinhibi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5(9), 2030.
[6]Yang, J., Wang, N., Gao, L., & Wang, X. (2021).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nd adolescent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Online disinhibit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s moderator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27, 106066.
[7]Wang, X., Qiao, Y., Li, W., & Dong, W. (2022). How is Online Disinhibition Related to Adolescents’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Empathy and Gender as Moderator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42(5), 704-732.
[8]Suler, J. (2004).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7(3), 321-326.
[9]易旭明,章岸婧 & 姚燕婷.(2019).理性与喧哗:大学生卷入“微博暴力”现象调查. 中国青年研究(03),102-107+73.
[10]邱獻輝. (2014). 建構霸凌行為之需求類型研究. 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 6(1), 1-32.
[11]余俊宣, & 寇彧. (2015). 自私行为的传递效应. 心理科学进展, 23(6), 1061.
[12]Zhou, Z., Tang, H., Tian, Y., Wei, H., Zhang, F., & Morrison, C. M. (2013).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34(6), 630-647.
[13]Lapidot-Lefler, N., & Barak, A. (2012). Effects of anonymity, invisibility, and lack of eye-contact on toxic online disinhibi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2), 434-443.
作者:阿蓝
编辑:Emeria、翻翻、游识猷

本文来自果壳,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如有需要请联系sns@guokr.com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 1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7904075
- 2 日本附近海域发生7.5级地震 7808816
- 3 日本发布警报:预计将出现最高3米海啸 7714622
- 4 全国首艘氢电拖轮作业亮点多 7616654
- 5 课本上明太祖画像换了 7521766
- 6 中国游客遇日本地震:连滚带爬躲厕所 7424490
- 7 亚洲最大“清道夫”落户中国洋浦港 7330256
- 8 日本地震当地居民拍下自家书柜倒塌 7238891
- 9 熊猫宝宝聚餐横七竖八躺成一片 7141500
- 10 “人造太阳”何以照进现实 7040370







 果壳
果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