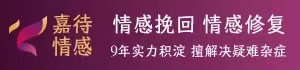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了一条通告。
这条通告全称为:《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所有看得懂的人看到后都长吁了一口气:终于要开始算总账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订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落下帷幕。战争虽然结束,但世界遍地残垣,硝烟虽然散去,但冤魂仍在哀泣。麦克阿瑟的这份通告发出,意味着这场清算审判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负责审判日本战犯的机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
“我政府业已派定名法官梅汝璈、向哲濬二氏为首批出席代表,向氏将任该庭检察官,梅氏将任审判官,闻二氏日内均将首途赴日。”作为二战中受日本伤害最深,损失最重的中国,自然要派出自己的代表。这场很多中国人认为胜券在握的审判,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按照规定,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来自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印、菲十一个国家,每个国家各提名一名法官,由麦克阿瑟任命,共同组成审判庭。还没开庭,一个事先谁都没想到的问题就发生了:十一名法官的座次怎么分?
远东军事法庭的章程对法官的座次并没有明确规定。一开始,大多数法官也没把“座次”当回事,中国派出的法官梅汝璈认为,就按当时盟军在“密苏里”号舰上盟军受降时签字的次序来不就行了:美中英苏澳……但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卫勃却表示:他希望他亲近的英国法官和美国法官坐在他左右两边——这样一来,中国就等于是排到了第三位。中国法官梅汝璈当即表示反对:在整个远东战场,中国是抵抗日本侵略最久,付出代价最大的国家,也是在密苏里号上第二个签字的国家,绝不能降到第三位。梅汝璈在开庭首日。当时他42岁,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时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一时之间,大家也都开始争了起来,有的说以英文字母排序,梅汝璈甚至开玩笑说,“如果这样,那就按体重排好了”。
对于座次排序争论,庭长卫勃一开始并未表态。但到了5月2日下午四点的开庭彩排仪式预演合影时,他却宣布:
“座次排列顺序为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新西兰和菲律宾。”梅汝璈当场起立离席,回到办公室,脱掉法官袍准备离开。
“英美法官对英美法系更熟悉,所以安排在我左右,这样工作起来更方便,没有歧视中国的意思。”“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这样安排是盟国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多、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他应有的席位竟会降低到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样的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是最高统帅做出的。”卫勃无奈之下,请梅汝璈先出去彩排拍照,晚上再做商议,但梅汝璈还是坚决拒绝:
“摄影师和新闻记者今天肯定都会拍照,这些照片如果传回国内,广大民众甚至会责难我的软弱无能。所以,我绝不出席彩排。政府如果不支持我,我辞职,请他们另外派人。”看到梅汝璈如此坚持,卫勃三次离开房间去找人商议,最终决定同意梅汝璈的意见:十一位法官合影。右二为梅汝璈,正是法官左手的位置。一个小小的法官座次问题,就已经需要如此博弈,可见这场东京审判,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事实也证明:在5月3日正式开庭后,各种困难和挑战接踵而来。
按照远东军事法庭最初的规定,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是从1941年“珍珠港事变”开始的。这显然是从美国人的视角做出的决定:美国在1941年12月8日正式向日本宣战。
但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来判定,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1941年之前,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就不能起诉和追究了。代表中国的检察官向哲濬站了出来,向法庭提出最强烈抗议。
向哲濬认为,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至少要往前推到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在此后,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军侵略中国各地,烧杀抢掠,屠杀了千百万中国平民,这些当然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向哲濬在东京审判中。向哲濬,当时54岁,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学士,时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被委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目前网上公开材料大多为“向哲浚”,他的儿子向隆万表示应为“向哲濬”。)在中方团队的坚持下,法庭最终决定以1928年1月1日作为起始日。但这又带来了另一个变化:时间提前了13年,中方团队就需要再多拿出13年的证据。
事实上,原先很多中国老百姓甚至官员都以为,日本侵华战争是全世界皆知的事情,惩治日本战犯也只是走个程序而已——当初很多中国人认为这场审判最多也就几个月就能结束了(后来审了足足两年半)。但是,东京审判适用的是英美法系:无论是不是战犯,先是“无罪推定”,然后需要在法庭上一条条拿出证据才能判定。而国民党政府最初只是以为,事实清楚,铁证如山,只要法官、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严惩战犯,所以并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物证材料。所以在开庭后,中方发现,每个日本战犯不仅有日本律师团,主导审判的美国还为他们指派了美国律师。相形之下,中国方面之前太乐观自信了——整个中国法律团队加起来不到20个人,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关键时刻,向哲濬紧急回国求援,要求再派几位得力的人去东京。刚考察欧美法律体系回国的倪征燠(yù)随即领命,以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的身份带领人手奔赴东京。倪征燠,时年4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1984年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是中国第一个国际大法官。倪征燠到达东京后,就和同事赶到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日夜抄写,翻译。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既然你们要证据,我们就给证据,而且要多用你们日本人自己保存的证据。
为了逃避罪行,日本战犯在东京审判法庭上做了大量伪证。对南京大屠杀的第一责任人、时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的审判就很有代表性。1946年12月29日,远东军事法庭开审日军在侵华期间制造大“南京大屠杀”案。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当时擅自决定进攻南京的松井石根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本人在法庭上表示:“攻打中国南京,我是受命行为,我本人是无可奈何的。”而他的随员冈田尚在作证时声称,1937年12月18日日军南京入城式的第二天,松井石根“满面痛苦”地对他说:“三十余年来一贯的愿望就是实现中日两国的和平,现在却是兵戎相见的悲惨结果,无限遗憾。”结果,法庭初步审判结果是:否定了检方提出的松井石根39项罪名中的38项,仅仅认定他在普通战争罪中对部属行为约束的“不作为”一项有罪。面对这个荒谬的判定,向哲濬当庭展示了一叠资料,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伯烈当时的报道、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当时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及现场拍摄的罪证。随后,向哲濬向庭长出示了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命令称:“占领南京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此外,中国团队还出示了松井石根在“南京攻略感怀”的日记中记录的话:以及12月21日松井石根回到上海后,在当天日记中的另一句话:“上海出发以来恰好两周,完成了南京入城的壮举,归来的心情格外舒畅。”在土肥原贤二出庭受审时,一个为他辩护的证人是他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他说:倪征燠在庭上立即反诘,拿出一份证据:1935年,土肥原企图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此事被外国报纸报道,而且将此事签名登报的,正是爱泽诚。爱泽诚随即低头不语。在诸多对土肥原有利的证言都被中方一一驳退后,最后时刻,土肥原居然放弃了个人辩护权利。当时有日本媒体分析:土肥原这样做,是避免被中国检方拿出更多的证据来击破。而在审判“九一八事变”元凶之一的板垣征四郎时,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当晚指挥的日军联队长岛本,他说:“当年犯下上述各种罪行,是不是就是现在坐在被告席右端的这个人?”“这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在每天繁重的庭审任务之外,中方团队还抓出了不少“漏网之鱼”。时任检察官秘书兼翻译的高文彬,当年才24岁,负责每天早晨整理前一天的庭审记录,贴好标签放好;同时还要为向哲濬准备当天开庭的资料。有一天,在整理资料的时候,高文彬在《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日本的《每日新闻》)的报纸上发现了一篇报道:在日军由上海行进至南京的路途中,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第三大队少尉野田毅突发奇想,与另一名少尉向井敏明打赌:谁先用刀砍死100个中国人。报纸前后详细记录了这场令人发指的“百人斩”比赛的时间、地点、杀人过程,并配有照片,最终野田毅杀了105人,向井敏明杀了106人,于是两人又相约,以谁先杀到150人再展开竞赛……
看完报道后,高文彬气得浑身发抖,立刻让人将这份报道复印三份,一份留在国际检察局办公室,另两份通过倪征燠转寄给了当时的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报纸后,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要求。由于这两人是日本低级军官,在日本投降后都已经被遣返,重新回到了百姓人群中,再加上同名同姓,所以寻找工作非常困难。经过半年的艰难寻找,最终在日本埼玉县发现了这两名当年的刽子手——他们已经脱掉了军装,头裹白布,做起了小商贩。1948年1月28日,井敏明和野田毅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证据确凿,判处死刑,被带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一个是谷寿夫,他当年是侵华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率部攻入南京后放纵部下烧杀抢掠,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元凶之一。他虽然被远东军事法庭列为乙级战犯,但被中方强烈要求引渡回中国受审,最终判处死刑。另一个叫田中军吉,他时任日军第6师团第45联队上尉连长,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屠杀300多名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和缴械军人。照片中的持刀者即为田中军吉。这张照片被日本军官山中峰太郎编入《皇军》一书,有名有姓有照片,证据确凿。在当日行刑前,曾叫嚣自己“杀过无数支那人”的田中军吉,大小便失禁。东京审判自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期间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最终,有28名罪犯被列为甲级战犯。很多日本人当时抱着好奇的心情参加了旁听——他们从来不知道,当初慷慨激昂的家乡子弟高喊“天皇万岁”后出征,在别国的土地上做出了那么多泯灭人性的事。在东京庭审期间,不少日本民众确实心怀歉疚,有些人看到中国人会立即低头,不敢目光直视。但按照最初庭长卫勃的意见:所有战犯,没有一个将判处死刑。在十一名法官中,像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这些国家,本土并没有被日本侵略过,而像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虽然和日本有过交战,但规模并不算大,也谈不上惨烈,而有些国家国内已经废除了死刑,所以他们并不赞成判处那些战犯死刑。卫勃提出的建议是,像当初欧洲流放拿破仑那样,把日本战犯流放无人海岛。而印度的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的观点更是石破天惊,他认为:侵略战争的追诉主体是国家,不能追诉个人;所有现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律,都是“事后法”,而法律不追溯过往;日本对侵略战争应负道德责任,但不应负法律责任……他甚至认为“南京大屠杀”期间松井石根因为患病所以“限制了行为能力”,应该从轻判处。
日本“靖国神社”中供奉的印度法官帕尔——他是“靖国神社”中唯一被供奉的外国人。此外,在日本建有帕尔纪念馆。帕尔在第一天庭审开始前,就向每一位日本战犯双手合十行礼。他的意见书长达1235页,之后还写过60万字的《日本无罪论》。后来在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支持下,帕尔三次受邀访日。
2007年8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访印期间会见了印度法官帕尔的长子普拉桑塔·帕尔。安倍在会晤中说,帕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表现出“高贵的勇气”,“至今赢得许多日本人的尊敬”。在11名法官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态度是最坚决的:必须判处死刑!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明,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展现了灭绝人性的一面,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纳粹德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如果这些日本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在梅汝璈的坚决要求和慷慨陈词下,日本的七名甲级战犯最终被判处绞刑,他们分别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
因为是无记名投票,也没有录音,至今没有人知道当时的投票具体情况。在东京巢鸭监狱关押的七名甲级战犯被分为两批,送入行刑室。
在行刑前一晚,七名甲级战犯都可以要求“最后的晚餐”,但除了东条英机要求了日本料理外,其他六人都表示没有胃口,忙于写遗书和与监狱请来的法师做最后谈话。
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都在遗书中写到希望今后中日和平,土肥原贤二写道“我祈祷上苍使中韩两国繁荣兴旺”,而东条英机写了两封遗书,一封给家里,写的是“不语一切”,一封给世界,依旧宣称日本发动战争是出于所谓“自卫”。第一批进入行刑室的是武藤章、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和东条英机,四人各自上四个绞刑架,同时行刑。
第一个死亡的是土肥原贤二,死亡时间是12月23日凌晨0点07分30秒。三分钟后,东条英机死亡,他死前曾双腿不停颤抖。在绞刑架上挣扎时间最久的是松井石根,他在脚下踏板被抽空后挣扎了12分30秒才死亡。
上午7点45分,7名甲级战犯的遗体被送至横滨市立火葬场,在熊熊大火中被化为一缕缕黑烟。东京审判的最后判决书长达90多万字,原本应为统一撰写,但其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部分的撰写,经过梅汝璈的坚决争取,由他代表所有中国人民自己书写,长达10万多字——“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在审判结束后,梅汝璈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其中有一段话:“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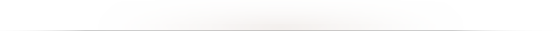 事实上,东京审判虽然是一次“算总账”,但算得并不彻底。这是一场伸张正义和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审判,但诸如日军的生化武器罪行、731部队罪行、强征和迫害慰安妇罪行、强征劳工罪行等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和追究,包括一些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战犯战后没多久就被假释了,甚至逃脱了处罚。尤其是日本战争责任体制中的最高责任者——裕仁天皇没有在东京审判中被追责,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之后日本政坛的怪相种种,以至于如今日本右翼开始对历史堂而皇之地否认和篡改。但毕竟有些事情,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是全世界都公认的,是历史有了定论的,比如被处死的七名甲级战犯,他们的罪行,他们的定论,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事实上,东京审判虽然是一次“算总账”,但算得并不彻底。这是一场伸张正义和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审判,但诸如日军的生化武器罪行、731部队罪行、强征和迫害慰安妇罪行、强征劳工罪行等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和追究,包括一些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战犯战后没多久就被假释了,甚至逃脱了处罚。尤其是日本战争责任体制中的最高责任者——裕仁天皇没有在东京审判中被追责,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之后日本政坛的怪相种种,以至于如今日本右翼开始对历史堂而皇之地否认和篡改。但毕竟有些事情,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是全世界都公认的,是历史有了定论的,比如被处死的七名甲级战犯,他们的罪行,他们的定论,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确实是矛盾且复杂的:两个国家一衣带水,却又一衣带血,历史上既有血海深仇,但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却又有阻隔不断的各种交往、交流和互惠互利。你们祖辈欠下血债,自然不可能世世代代找你们的后人追索,大家可以一起向前看——这是在你们承认过去错误的前提下。但是,这笔债是不可能忘记的,是需要铭记的。更何况,你们有些人如果还不认账,甚至要翻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需要世世代代鞭策乃至动用必要手段提醒你们的。而那些甲级战犯,梅汝璈也有过定义——是“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在东京审判期间,中国的法官们费尽心力,拼尽全力,终于清除了不少,但他们也知道,一时之间,是清理不完的——梅汝璈自己也只是谨慎地说,即便清理掉,也只是相信对中日和平“必有贡献”而已。如今,这些曾经的“绊脚石”依旧被一些日本右翼供奉在“靖国神社”里,出于各种原因,我们只能严正抗议。但是,如今在中国,在南京这座有特殊历史记忆城市的寺庙里,居然出现了这些“绊脚石”的牌位,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无论是什么理由和动机,无论是“超度”还是“供奉”,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这不仅仅是“搬别人的石头砸自己的脚”,更是用别人的刀剜向了自己同胞的心。
1973年,梅汝璈逝世。三年后,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厚达一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1、《东京审判:中国学界的观察与思考》(耿显家,《史学月刊》,2020年03期)
2、《梅汝璈与东京审判》(《中国民族博览》,2020年11期)
3、《东京审判后传:大法官梅汝璈的最后25年》(高渊,微信公号:“水米糕饭局”)
4、《重新发现东京审判》(徐持,《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02期)
5、《正义与邪恶的交锋——亲历东京审判》(张林凤,《炎黄春秋》,2020年9月)
6、《民国媒体中的东京审判》(刘广建,《档案与建设》,2019年08期)
7、《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官》(韩啸,《中国检察官》,2018年11期)
8、《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及其影响》(郭小鹏,《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1期)
9、《东京审判与“帕尔神话”》(宋志勇,《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06期)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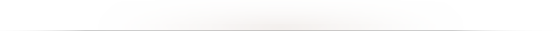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广东共青团
广东共青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