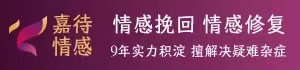张腾岳:《走近科学》就不是为那些看原版Discovery的人准备的



央视主持人张腾岳已经接受了90后、00后送给他的标签——“童年噩梦”。
偶尔,他也会半开玩笑地分辩几句:“你们传来传去的那些稀奇古怪事我大多数都认,不过‘种白萝卜,得红萝卜’‘房子到处带电’真不是我做的。”
《走近科学》是张腾岳媒体生涯的起点。作为“科教兴国”战略的产物,这档科普节目诞生于1998年,正值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科学院前院长郭沫若发表《科学的春天》演讲20周年。

从跟踪报道“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到推介蓖麻油催产餐,从数学家吴文俊到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刚刚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张腾岳那时整天被中科院“大牛”和中国最新锐的科研成果包围,甚至刚刚创建北京三七二一科技有限公司的周鸿祎也在其采访对象之列。
社交平台上有关《走近科学》的讨论,则更多围绕其2004年改版后一系列“开头悬疑,结局‘狗血’”的选题展开——夜半萦绕在广西岑溪一幢“鬼楼”中的怪声最终被证明是由钻进化粪池的鲇鱼发出;
飞蛾之所以被某药厂的监控拍出“外星生物”般的灵异感却不为肉眼所见,是因为摄像机的快门速度被调成十二分之一秒;
随时吐血、能从身体任何部位吸出血来的“吸血怪物”,只是普通的牙龈炎患者……

而张腾岳留给普罗大众的深刻印象,是入夜时分电视机里与阴森配乐交织在一起的低沉男声。
《走近科学》由此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蜕变为亚文化现象。
当网友们争相在十几年前的节目视频中翻找“最恐怖的那几集”,张腾岳本人也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中不负众望地熟练使用被数度恶搞的“《走近科学》体”——“这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引发爆笑。
但面对“以科学之名博眼球”的批评,他曾经认认真真地同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看探索频道(Discovery)和美国《国家地理》长大的年轻人抬杠:“大哥,您一个可以看原版的,揪着《走近科学》干什么?您这不闲的。”
张腾岳以《走近科学》监制孙素萍对节目名称的诠释回应种种非议:“作为一档科普节目,我们只能力求贴近原理,却不能像科学家作报告、写论文那样完完全全进去,况且我们把最权威的成果拿出来,老百姓也不一定看得懂。”
他坦言,借助电视手段把科学问题解释清楚,本来就是个麻烦事,但在知识获取途径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传播形式恰恰是科普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下为张腾岳口述。

成功的节目必须首先讲好一个完整的故事,
甚至要具备矛盾和戏剧冲突
前两天去故宫,我看见一个妈妈指着东华门上形状不规则的脚钉对孩子说:“看到没有?那个是被机枪打的。”我不禁想起在宁夏沙坡头排队等乘羊皮筏子时遇到的另一个妈妈。
她问:“羊皮筏子里推的是氢气吧?就是人呼出来的那种。”大概是声音太大了,大概是当着太多人的面,孩子爸爸看上去明显有些生气和窘迫:“人呼出来的是氢气,那羊皮筏子还不得飞上天去吗?记着,里面是二氧化碳!”
这两段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经历纠正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误解,即你烂熟于心的常识可能是其他人所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做《走近科学》的时候,给自己定了个“雅俗共赏”的目标,说直白点,要让老百姓记住,咱有病了不能自己瞎吃药,一旦手上划了个大口子、烫了个大水泡,得正确处理,不能撒一把香灰、抹点儿酱油或肥皂了事。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不“高大上”?但电视节目不是现在的视频,它有严格的播出时长控制,要求你在30—40分钟里把复杂的科学道理讲得简单、清楚,还要让观众爱看,这就是个难题了。
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大众传播的受众特点就决定了很多议题不能通过这个途径流行。
与网民的印象恰恰相反,《走近科学》做过很多重大选题,比如我们可能是中国第一支深入探秘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媒体团队,也曾经派出两个导演跟随中国探险队登上南极冰盖之巅(Dome-A)。

就我本人而言,因为做《恐龙大调查》,把中国但凡有恐龙的地方都跑过了,和你们现在都很喜欢的网红“嘤嘤怪”、古生物学者邢立达早就认识。
但你说“百千万人才工程”这事重不重要、有没有意义,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大家伙不爱看。
就像对致力于科技宣传的媒体作出嘉奖的法国儒勒·凡尔纳奖,我们拿过好几回。业内说好,观众就喜欢吗?未必。
所以收视率这个概念渐渐引入之后,老一辈电视人因为没有更多办法掌握跟观众沟通的渠道而产生的闭门造车问题就日渐凸显。
在数次改版都不是很成功的情况下,当时人气节目《讲述》的制片人张国飞调来了《走近科学》,他的一些观点我至今都非常认同。
他认为,成功的节目必须首先讲好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框架齐备的情况下,还要有相应的矛盾和戏剧冲突等,其次才是讲解科学知识。
老百姓看电影的时候不纠结特效花了多少钱而关注情节如何,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可以长篇大论、事无巨细地介绍一项科学工程,但不是期期必须如此。
理念转换之后的效果特别明显。我们的工作地点有一块大板,会把不同节目每天的收视率晒出来,2004—2006年期间《走近科学》平均收视率达到0.48—0.51,搁今天看也非常亮眼。

当然,被网友们频繁议论的那些“童年噩梦”也是在这个时段集中面世的。其中一个被密集吐槽的点是“搞了半天你就给我看这个”,事实上,这是表述方式与心理预期的问题。
拿峨眉山那个因为屋顶从来不沾落叶而被当作神佛显灵的大殿为例,其原理是特殊的地形导致空气经过时会形成小风扇式的效果,从而把树叶撵下来,概括起来不就成了“被风吹的”?
这和魔术揭秘差不多,看着邪乎的东西掰扯清楚了,往往令人失望,因为心理预期没有实现。
心理预期带来的另一种后果是,对于一些尚未产生结论的谜题,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科研成果和知识储备作出讲解、推测,但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往往就成了结论。
就像《走近科学》做过的中国UFO调查系列,我个人觉得起码我们前所未有地对这个议题作出了探索的尝试,但很多观众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没在节目里看到类似“真有外星人,还抓了活的”那样的戏码。

那我得老老实实承认我们真没抓住过,到现在为止“51区”都不敢说自己抓过。
这正是科普工作的矛盾所在:公众把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编创的电视片《宇宙》称为“神作”,但反而在观看《生活大爆炸》时高效地记住了许多专业词汇,正如《走近科学》被他们记住的,往往是那些看上去特不科学、特怪力乱神的部分。
有意思的是,探索频道过来跟《走近科学》合作的时候我们有导演问“科学节目应该怎么做”,对方就强调,他们的自我定位从来都是“娱乐节目”而非“科学节目”。
令人吃惊之余,道理其实没错——电视这种传播手段没有别的,一个是信息,一个就是娱乐,这是必须把握的根本原则。

互联网拆掉四处林立的知识壁垒,
并提供了更多、更灵活的选择
2013年之后,台里对节目内容的划分日益细化,医学、考古、特色养殖这些部分开始由专门的栏目接手,《走近科学》逐渐回归创办初期那种关注前沿成果的状态。但节目的调整其实反映了大环境的变化。
首先,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在这个阶段确实有了显著发展,不仅集中涌现了一批“大国重器”,而且普罗大众越来越容易享受到科技给生活带来的福利、便捷,某种程度上来说起到了一种提振民心的作用,至少整个社会对科学是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感兴趣了。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我刚做《走近科学》那阵子有中科院院士给我讲课,说咱们目前是“骑着骆驼赶鸡”——造得出卫星、飞船、潜艇,但造不出圆珠笔头、伞骨钢丝。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把以往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或者说四处林立的知识壁垒拆解了,而且提供了更多、更灵活的选择。
说到这点,其实以往中科院和中国科协都做过不计其数的科普工作,但效果并不明显,毕竟那些在研究领域达到世界顶尖级别的专家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普通人几乎没有交集,就像小学老师讲加减乘除会比数学系教授更专业。
相比之下,互联网可以不受时间、空间、形式的限制,随时提供资讯,引发讨论,而且它从本质上而言是建立在“共享”基础上的,即人人皆可参与上面所说的提供资讯的过程。
那么我们就发现,科学从原本自上而下灌输的知识变成了“热门话题”,而在其中扮演着引领者角色的,就是知乎、果壳网、科学松鼠会等平台上那些既相对专业,又很懂得用大家能接受的语言节奏来表达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一方面能帮你筛选、消化特别难啃的学术资料,然后用你喜闻乐见的形式比如答问体、信息图、视频,把事情讲清楚;
另一方面,他们能带着你在他们擅长的知识领域内玩得特别爽,比如@林瘦猫 是搞化学的,@天师-卡赞 是搞气象学的,@开水族馆的生物男 对鱼类特别了解,@二宝-杨毅 就天天带你上动物园看稀奇古怪的动物,还有写宝石鉴定写了整整9年的……
这就特像那些摆弄手办的,能给你讲得头头是道,这是哪个ACG作品里的、这是第几代,在不痴迷于此道的人看来,无非归结为一句话——“花钱玩这小人儿,什么事儿啊。”

但无论如何,科普的分流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众口难调”已经不再是需要顾虑的首要问题,只要能持续满足对某一领域有兴趣的那群人的需求和关注点,一个科普媒体就有存在的价值。
而对于受众来说,互联网已经彻底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不仅令他们知道了越来越多的东西,更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中还存在许多盲点。
他们有越来越多的途径来补足自己的盲点,比较、印证自己获取的信息:带孩子逛公园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植物,只要拍张照片上传到相关App,几秒之内就能给你详细介绍;
夜晚天好能看到星星的时候,只要打开定位,相关App就能告诉你那些星星的名称……
当颜值、家庭背景的差异不能轻易改变,知识反而成了这个时代最容易获取的财富。
这就给科普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他/她不再是一个机械的训导者,而必须有很强的同受众互动的能力,所使用的语言、所采取的方式,都应该让大家愿意聆听,至少得紧跟当下的语境;
他/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搬运工,而必须做到专业,因为检验他/她言论的机制层出不穷,就像我提到的那些科普大V,拿出来的基本上都是自己领域的一手知识;
最关键的是,他/她还必须利用形式多样的传播手段,顺应受众心理和传播规律。

 如果教条主义地把科学当作信仰或者指导思想,是失之偏颇的
如果教条主义地把科学当作信仰或者指导思想,是失之偏颇的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讲过一个故事。关中人不识螃蟹,有人收得一只干蟹,街坊见这种生物外形甚是丑陋奇异,就借去挂在门上,以期吓走“疟鬼”。
关于“疟鬼”,韩愈的《谴疟鬼》诗写道:“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古人理解治疗疟疾的有效手段,是同时包括医术和巫术的。
先别急着看咱老祖宗的笑话,欧洲人的“放血疗法”听上去也很荒谬。
史料记载因放血疗法而殒命的名人有好几个,比如英国诗人乔治·拜伦勋爵。

“地理大发现”之后,原产于安第斯山脉的金鸡纳树皮作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被介绍到欧洲,即使这样,还有人认为它是“魔鬼的药粉”,是耶稣会教士用以毒害国王的阴谋。
英国“光荣革命”的关键人物、军事家克伦威尔患疟疾时就拒绝使用金鸡纳树皮,直至死亡。
再后来,金鸡纳树皮被氯喹取代,但人类仍然不知道疟疾的起因,哪怕发现了疟原虫,其传播途径也依然成谜。
人类认识疟疾的过程多少反映了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其实科学就是我们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的一种模型、一种工具,如果教条主义地把它当作信仰或者指导思想,是失之偏颇的。科学首先可以被证明。
比如中药,也许从西医的角度讲它不是科学,就像说人中白、人中黄、金汁能治病一样,玄得很,但毕竟《本草纲目》中很多药的疗效是李时珍亲自试验过的,即使没有上升到演绎法、归纳法的阶段,也可以说是经验产生的科学,你不能否认它存在的价值。
其次,科学是不断发展、不断更新、不断修正、不断被推翻的一个流动的体系。200年前你告诉我铁做的东西能在空中飞,我会觉得你疯了。
因为在当时的人的认知中,比空气重的玩意上不了天,直到滑翔机、热气球出现,才打破这种认知。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例子则是,现在一个孩子就能随随便便纠正你从小建立的常识——“太阳系只有八颗行星,而非九颗”。
而被你当作笑料的甩手疗法、鸡血疗法,还有头上顶着一口锅从北京妙峰山接收宇宙气场的气功学员,在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可是引发全民热潮的正经“高科技”。这种来自后辈的嘲笑和鄙夷,恰恰证明人类始终在进步。
所以,不要以为“走近科学”的要义是得懂很多知识,这在当下并不现实,也没必要。

我们每天都使用遥控器,但只有极少人知道爱因斯坦正是因为解释了遥控器工作的基本原理——光电效应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就像我现在问你从空调到冰箱的制冷原理是什么,你能给我攒出来一个么?如果不是因为遇到故障请人检查过设备,你可能什么也答不上来。
即使是18、19世纪那些横穿非洲、深入极地、满世界探险的“博物学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主要成就可能还是在科学传播方面。
更何况,科学和知识本来就没有太大关系。去年美国人麦克·休斯发射了自制火箭以证明他一直支持的“地平说”,用和科学家们同样的手段去证明截然相反的结论。它归根结底是普遍意义上的“存疑—证明”态度,或者说,是对改变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记得之前做航天类选题时,有杠精问我这些玩意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有没有关系。讲真,欧阳自远或杨利伟也不能给出详细的解释,但我可以勉强地回答他们:有。
其实天文也好,生命起源也罢,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而言就是兴趣,但我们会因此而陷入沉思,展开联想,把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经济积累和科学技术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指向星辰大海的探索雄心就会应运而生,这和我们兜里有了钱之后想出国去看看是差不多的。
好奇心永远是人类内心最简单的驱动力,无论什么时候都如此。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47期
✎作者 | 卢楠
欢迎分享文章到朋友圈
新周刊原创出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规则的游戏与游戏的规则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 1 中法元首相会都江堰 7904746
- 2 中方不接受日方所谓交涉 已当场驳回 7809641
- 3 大闸蟹为何会在欧美泛滥成灾 7712093
- 4 国际机构看中国经济 关键词亮了 7618457
- 5 家长称婴儿被褥印不雅英文单词 7521851
- 6 日方军机滋扰擅闯或被视为训练靶标 7424661
- 7 罪犯被判死缓破口大骂被害人一家 7332613
- 8 国乒8比1击败日本队 11战全胜夺冠 7237709
- 9 长沙一男子要取现20万 银行紧急报警 7137013
- 10 千吨级“巨无霸”就位 7042279









 新周刊
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