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好的电影,其实是你我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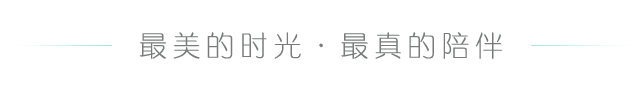
点击上方“青年文摘”
右上角“...”点选“设为星标”
点击加星★?贴近你心??
作者:门纪
来源:新周刊(ID:new-weekly)
1895年,圣诞节刚过不久,卢米埃尔兄弟准备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的地下室里,放映自己拍摄的短片。受邀前来的法国社会名流,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最早的一批“观影人”。
一年后,中国上海徐园,常见有人挤在“又一村”茶楼的一角,看西洋影戏看得津津有味,啧啧惊奇。
京剧老生演员谭鑫培和琴师、鼓师一同,合作了自己拿手的《定军山》片段,北京丰泰照相馆最好的技师负责把这些画面记录下来。后来,片子在前门大观楼放映,前来观看中国第一部电影的人络绎不绝。

电影《定军山》剧照
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建造的虹口活动影戏园,在上海乍浦路开张。由此拉开了“东方巴黎”“东方好莱坞”的繁华序幕。
电影诞生至今不过百余年时间,但这亦是整个人类社会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发展最为迅猛的百余年时间,而中国电影人与中国观众始终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
当年,在卢米埃尔兄弟50秒的短片《火车进站》中,火车从右上方的景深处远远驶来,划过整个镜头,就好像要冲破银幕一样。不少观众还大吃一惊,赶紧起身躲避。

世界上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片中的人物是一百多年前的人
今天,看电影已然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最稀松平常的一部分——百货商场标配一间电影院,年轻人谈恋爱的经典流程是“逛街吃饭看电影”,当你填写个人简历时,即便是再想不到自己有啥爱好的人,也会在“兴趣”一栏中写上“看电影”……
原来,电影工业也早已像默片中的那辆火车,冒着腾腾蒸汽,悄无声息地,撞入了我们的生活。
它曾经是一门遥远的艺术,银幕上的人一板一眼,银幕前的观众正襟危坐。后来,它变成生活的回响,透过镜头,观众能窥见自己的身影。
而今,光影呼啸,年轻的面孔轮番登场,电影看得多了,电影里的世界倒好像离普通的中国人更远了。
经历了电影角色一点一点贴近普通人,又渐渐两脚离地的过程,看着这列火车驶近又驶远,坐在电影院里面对着索然无味“大片”的中国观众,盼望着它重新回归。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电影刚来到中国时,带着一层天然的高端滤镜,与普通人的生活相疏离。
在中国电影产业尚不发达的时代,大量的译制片增加了这种陌生感,强化了观众的某种印象:电影里的人高鼻梁蓝眼睛金头发,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1950年夏天,《大众电影》杂志创刊,面向中国电影工作者与影迷,提供资讯、深入报道与影评。第一位登上杂志封面的,是苏联电影《团的儿子》中的男主角“伐尼雅”。

《大众电影》创刊号封面
伐尼雅是苏联作家卡捷耶夫笔下的一位“小英雄”,聪明又倔强。影片讲的就是他帮助苏联红军的骑兵战士打败了德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上映的电影中大量涌现了“伐尼雅”式的英雄形象——
由鲁莽冲动的小八路成长为真正革命战士的董存瑞,带领黑龙江老百姓开荒剿匪的老军人战长河,带领农民要在地主的平原上卷起风暴的朱老忠……
他们在电影中完成的战斗、胜利与成长,与银幕外老百姓告别黑暗过去,欢欣迎接新时代的当下相吻合。
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发生的转变,也在观众中发挥出强大的共情能力——当然,这种共情通常还是仰望的,这些英雄式角色,与普通人的生活还相去甚远。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是当年颇受好评的一部影片
每当夕阳西下,放映员将幕布架好,大家便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板凳放到黄金观影位置。有些人住得远,翻山越岭,赶了几十里路也要过来看电影。
好位置是盼不上了,满满当当的观众从四面将银幕围住。再后面一些的人都不用板凳了,干脆爬到屋顶上、电线杆上,因为看电影太过入迷而摔一大跤也是常有的事。
1963年,受苏联电影《伊凡的童年》的影响, 崔嵬导演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的小兵张嘎。虎头虎脑的嘎子哥在白洋淀闹出不少笑话,但他又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一度成为众多50后、60后争相模仿的“偶像”。

小兵张嘎,是一个不同以往的革命战士形象
影片宣传资料是这么介绍小兵张嘎的:歪戴破草帽,手拿木枪,身穿白褂,光着脚丫。他只有13岁,擅游泳,能爬树,会摔跤,爱咬人。机灵鬼透,野气逼人……
同年,上海《青年报》有文章报道,有孩子把铁丝弯成“小手枪”,把火柴头当火药装在上面,在别人耳朵边放得砰砰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嘎子哥也是一代熊孩子的“反面教科书”。
孩子忙于模仿偶像,青年人则充分利用看电影来找对象。
坊间曾这样形容七十年代的电影院:“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拥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日本电影内部发票。”一来二去放的都是那几部电影,谈的恋爱多了,台词都能背得出来。
但薄薄的幕布终归挡不住世俗生活的烟火气,在日复一日的单一题材影片里,观众解读出了别样的意义。

“快……快去救列宁!瓦西里……瓦西里是叛徒!”
作家叶兆言回忆,有段时间公映的外国电影只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有人多次买票,就是为了看《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那段《天鹅湖》。
据说《列宁在一九一八》是东北厂译制的,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所以无论是列宁,还是瓦西里,说话都自带一股东北味。
以至于人们说起影片中的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都会不自觉地模仿东北人。
更有传说,某些地方不允许银幕上出现过分露骨的镜头,所以当《列宁在一九一八》播放到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以及瓦西里夫妇拥吻的镜头时,放映员必须使出简单粗暴的剪片技巧——在恰当的时间用手挡住镜头。
七十年代末,高仓健的《追捕》播出,国内正流行的“唐国强式”奶油小生受到硬汉潮流的强烈打击,即便他们逢人便夸“你长得真像真由美”,也无济于事。

《追捕》1976年在日本首映,1978年引入中国公映
作家莫言曾和友人争论,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到底有没有赚得国人一万吨眼泪。友人是这么算的:中国当时看过电影的有1亿人次,每人流一两眼泪,一算就1万吨了。
1972年的秋天,莫言曾经饿一天肚子跑50里路,到电影院为花妮的故事热泪盈眶。
30年后,莫言再看《卖花姑娘》,他“一边看里面的情节,一边想象自己忍着饥饿往县城奔跑,想起当时那么年轻,那样有追求,为了看一部电影可以不吃饭”,便依然泪流满面。
让这个山东少年感动到涕泪横流的角色,从英武的革命战士变成了异国的少女,奔跑着的莫言那时候一定想不到,一个属于平民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

《卖花姑娘》剧照

中国电影的许许多多个“第一次”
八十年代属于启蒙,这一点在文艺作品上表现为人性的回归。具体到国产电影而言,就是宏大叙事的版图渐渐缩小,日常生活的题材渐渐扩大。
镜头一点一点放低,终于到了和普通人齐平的高度,我们能在电影里看到越来越多活生生的“人”——他们不再是简单的轮廓,单一的性格,而呈现出属于生活的多元和温度。
青年制片厂诞生,青年电影人开启了自己的电影语言探索之路,“第四代”导演登场。
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导演们组成了小团体,取名为“北海读书会”,并在誓词中写下:
1980年4月5日,时值清明,我们在北海聚会,相约发奋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






 一部《红番区》,让成龙与贺岁喜剧紧密相连
一部《红番区》,让成龙与贺岁喜剧紧密相连










▽?更多推荐阅读?▽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 1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7904245
- 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7808371
- 3 联合国厕所不再提供擦手纸 7714360
- 4 乘冬而起 向雪而行 7617530
- 5 哈尔滨机场出租羽绒服 洗2次不再租 7522908
- 6 外交部:高市的态度完全没办法对话 7426921
- 7 网警:男子AI生成车展低俗视频被拘 7329834
- 8 华为重夺中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 7237408
- 9 外交部:日方没必要大惊小怪对号入座 7143960
- 10 卓越工程师培养有了新标准 7042234







 青年文摘
青年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