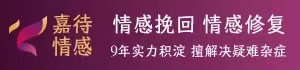新中国民营经济的隐秘源起


作者:楼台@来源:虎嗅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和毛泽东在主席的书房见面了。在现实主义的指引下,两位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各怀心思地坐到了一起。言谈间不乏诙谐幽默,只在云雾缭绕之中,风雷隐现。
一开始,尼克松恭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回答道:“我没有能力改变整个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这是一个颇为感伤但意味深长的回答。尽管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中毛泽东仍旧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巨人,但是他身体的虚弱已经是“显而易见”,时刻离不开身边的护士。会议结束时,尼克松看破不说破,还在宽慰毛气色不错,不过毛泽东耸耸肩,回答道:“表面现象都是骗人的。”
这是领袖的最大的心病, 他的后半生就在和欺骗作斗争。革命成功之后,他最担心的便是身边的“赫鲁晓夫”会颠覆他的政治遗产。即使在和他最大的意识形态对手和解之后,他也未曾放弃“扫清资本主义”的斗争,复出整顿经济的邓小平也再次下台。
但历史是反讽的,章奇和刘明兴两位学者在《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观察到:正是一轮又一轮意图消灭的私有制的政治风暴,分裂了严密的官僚体系,松动了国家对于基层组织的控制能力,让企业家精神在此发芽;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最高潮,红色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各地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之际,在某些地方基层私有制得到了空前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这本书可能是近年最具启发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完全颠覆人们对于中国治理的想象,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看似断裂的历史终于能够合二为一,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家的终极三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可以在这本书中得到启发。一定程度上,本文也是对章、刘两位学者的观察总结的简化、故事化和延展。
1
2004年秋,在无锡参观梅园的王石第一次听说了荣氏兄弟的故事,非常感慨。在龙井山下的浙江宾馆,问了吴晓波一个问题:
“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
吴晓波一时语塞。在普遍的历史叙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历经三大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私营经济和企业家作为阶层被集体消灭;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一般崛起,10年之后的1988年,民营经济在营业收入和就业上就已经占据半壁江山。
但这种时间逻辑暗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存在历史断层的,凭空消失,凭空出现。
不过,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言: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章琦和刘明兴提出一种天才的洞见:中国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精神并不是无根之木,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基层官僚和群众达成特殊的同盟对抗政治风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地方性的产权保护。
在浙江,强势南下干部和弱势的游击队干部的不同的政治生存和竞争策略,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土壤。
1949年之后,浙江的权力格局,是由随野战军南下的干部以及在本地游击干部组成。三大战役之后,所有人都知道国民政府败局已定。浙江的游击队趁机发展壮大,甚至出现了北方绝没有出现的、由游击队解放城市的壮举。
比如温州,1949年5月6日,温州游击队策动国军起义, 游击队干部就接管了温州城。当南下干部来到时温州时,发现并没职位空缺,只能移师丽水县。但是,不足一月,组织就做出了安排,游击干部让位,500多位南下干部就接手了温州的主要职位。
长期以来,浙江游击队和中央隔离,而南下随军干部则更为强势,所以游击队干部在权力格局中就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状态。但是,由于他们的革命成就和本地关系,所以在执行政策的基层部门存在感更强。
非常明显,南下干部和游击干部的权力基础是不同。南下干部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上级的授予,所以更倾向于无条件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游击干部缺乏上级的支持,只能够向下寻求当地群众的支持。
这种国家意志层面的政治动员,不仅是按照意识形态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也是体制内权力精英动员自身资源进行竞争的角斗场,官员们必须向上级证明自己的忠诚,向下层展示自己的权威,并且趁机削弱竞争者。所以,他们必须根据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建国之初的土改运动中,南下干部就积极执行上层的左倾路线,并且批评游击队干部执行政策不积极,犯了“和平土改”的错误,游击干部更是进一步的遭到打压,一些被调离职位,甚至有干部自杀。此时,一些游击干部向上申诉,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正是由于在权力格局中的孤立无援,游击干部就抛弃了走上层路线的幻想,开始走群众路线。有意思的是,虽然说他们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但却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最大的政治资源其实是体制外的基础群众时,他们其实更愿意消极执行,甚至暗中抵制一些“左”倾的政策。
“这就等于在当时看起来严密的政治和社会控制中撕开了一条缝,使得那些不被正统意识形态认可的异端经济形态的存在成为可能。”
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依靠农业集体化,小麦比1940年增产48%,粮食问题已经“顺利地解决了,永远地解决了”,受此鼓舞,中国也开始行动。
1953年,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换而言之,就是要在城市中推行国有化,在农村推行集体化。
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异常顺利,但在中共起家的农村,集体化却是一波三折。
农业集体化很大程度上是和统购统销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也是为了建设重工业对农民收取剪刀差,所以农民有抵触情绪。主管此事的陈云说:
“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尽管农业集体化名义上是以“自愿”“互利”为原则展开的,但是这成了地方能人施展手段媚上,积累政治资本的舞台。
1953年秋,大寨为了推行农业社,分了农业社和互助组两队,由于管理得当,陈永贵所在的农业社亩产240斤,远超互助组180斤,于是开大会给农业社唱赞歌。但是会上遭到了一个单干铁匠的反对:“你农业亩产240就大惊小怪,我这个单干户土地不如你,我一亩地产它300斤,也觉得没啥。”
当时陈永贵被噎住了,不过很快就想出办法, 动用了统购统销来打击刺头:
“国家要我们卖四万二千斤粮食,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咱们正想按照这个产量分下去,这回还不超额完成,你报三百,咱就按这个三百给你派吧。”
当时,农民卖给国家的粮食价格要低市场价17.9元。农民自然不愿意。铁匠立刻服软左右开弓自扇嘴巴。陈永贵当年超额上缴三千斤粮食,达到四万五千斤,第二年,一些家庭果然青黄不接。
但政治动员的力量是惊人的。1956年夏天,91.7%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其中62%加入了高级社;年底,96.3%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其中87.8%加入了高级社。但当时有党外人事提出“三九“的评价,90%的农民非自愿,90%的合作社产量更低,90%的农民生活条件恶化。
1956年的秋天, 全国各地就开始出现“闹退社”的现象,最亮眼的就是浙江。
浙江的永嘉县公开提出“包产到户”“责任制”,有人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承包制,将推行相关政策的干部视为孤胆英雄。其实未必,除了浙江,四川、广东、河南、云南等许多地区都发生“包产到户”,所以这很可能是一个全国现象,只是不存在纸面和官方文件上罢了。
但浙江永嘉县有其特殊之处,包产制作为一种正式的官方制度,它存在了10个月之久。在中央定性之后,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地下制度,它在永嘉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生命力极其顽强。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发布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打算在农业集体化上卡口子,这是根据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永嘉县根据这项文件精神开始实行包产制,产量提高40%,但是这个风向开始变化,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文《包产不可到生产小组》,但是永嘉县不退反进,还是公开在机关报上宣讲包产到户的好处。1957年2月,被人告上中央,高层一锤定音。7月9日,当领袖上海公开发布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之后,永嘉的包产到户再被叫停。不仅是参与的干部,戴洁天,李云河和李桂茂三人,遭到免职和参加劳改,更有10名农民被抓,高层态度非常坚决。21年之后,他们才获得了平反。
但是讽刺的是,根据永嘉官方记载,在1957年之后,“包产到户”不仅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1959年,官方就承认已经“死灰复燃”,1962年,176个生产队采用了包产到户。1967年,在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之时,游击队的干部也是敷衍了事。 196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5438个,涵盖77.3%的农户,1976年,6000多个生产队,80%的农户已经采用了“包产到户”。
其实,大规模的“闹退社”和”包产到户”主要都是发生在曾经的游击县;在非游击地区,即使是在大跃进时期,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已经非常明显时,干部仍然严厉禁止包产到户,导致了大规模的外逃。
游击干部对于基层群众的庇护在大跃进时期表现更为明显。当大多数南下干部都在媚上争宠时,游击干部则是更倾向于照顾群众利益,特别是在大跃进的后期;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干部就没有按照上级的指示征粮,而是给群众留下了足够的口粮,1960年,当中央作出可以保留一定的自留地之后,当地干部迅速将其公布,而温州地委是在1961年8月才正式批准农民拥有自留地。在萧山县,部分干部不仅会默许黑市交易,甚至会在粮食增产时,还减少上报,从而给农民留下更多粮食。
游击干部的策略很快得到了回报,在“大跃进”失败之后,1963年,中央发动了所谓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将权力外围的基层干部列为批判对象,鼓励群众揭发他们在大跃进时期犯下的错误。
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王洪文就曾因为不注重群众关系,在“四清运动”中吃了大亏。当时的王洪文不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最大的梦想不过是科长。虽然只是个科员,但是大小是个干部,加上平时为人也差,也就成了批判对象。
有人向工作组举报,王洪文平时一贯小偷小摸,例如捡外宾剩下抽剩下的高级香烟,偷厂里的黄沙,水泥、弹簧锁和公家的木料给自己家装修,就连身上衬衣都是偷厂里棉布做的,更有人要当场将王洪文的衬衣扒下来……
从公家顺点东西,其实是当时的常态,只不过王洪文群众关系太差,所以成为批判对象,自此科长梦碎。
这时候,游击干部的群众路线显现回报。群众也庇护了顶住左倾压力的干部。比如在乐清的柳市镇,上级的工作组用了三个月时间,也没能鼓动群众揭发、批判当地的基层干部。
在四清运动中,游击干部和地方群众都清楚了明白了自己在体制内生存的最佳策略,就是结成利益共同体,对抗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
在博弈论的视角中,合作的前提,是发出明确的合作信号,把看似常识的信息,变成共有知识,这样人才能达成合作,这也是皇帝的新装故事中孩子勇气的价值。不过,有时候,即使不能沟通,但通过具体的行为,也可以传奇清晰的合作信号, 言胜于行。
经历过大跃进和四清运动的考验,双方很快了解了对方的需求,开始了默契的合作。“四清运动”之后,浙江游击地区迅速地冒出了很多地下黑市。
“东阳县于1964年末开始形成棉花自由市场,其籽棉日交易量一度高达1.4万斤。另一个棉花黑市落在义乌县。仅在该县的佛堂、蒲阳两个集镇,每天上市棉花3000多斤。在黄岩县新桥区,从事土纺土织的有6000多户,占总户数的30%以上……1964年8月,该区市场以已上市96万尺,土纱6.2万斤。”
“在萧山县,从1963年开始,就出现大量的票证交易。仅乐清一县,就存在数个地下黑市,新街区的票证市场、孝顺区的木材市场、大桥头区的粮食市场,以及街头旅馆钱的土纱土布市场……还有人从事大规模的土麻袋贩卖活动,生意覆盖很广,外销到山东、湖北和内蒙,从事贩卖的一些大户日获利都在千元以上。”
这样看来,所谓万元户的概念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早得多。不过,尽管游击干部和基层群众达成非正式的攻守同盟,但是由于游击干部在权力格局中还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能对地方群众提供的产权保护是极为有限的。
但是,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省游击地区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转折——非公有制经济超过公有制经济。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初期,浙江省委还幻想将运动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却没有想到革命的对象就是自己。1967年1月,造反派在上海成功夺权之后,各地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浙江省以江华为代表的省委领导就被夺了权。2月11日,江华紧急乘坐周恩来安排的专机飞往北京,登机后才得知妻子已经自杀。第二天,造反派宣布其被撤职。
其实,江华的失势,本质是老上级谭震林及其他军队元老与“造反派”发生了冲突,被定性为“二月逆流”,然后被打倒。自此,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为实际的权力中心,江华自然失势,南下干部更是被冲击的七零八落。浙南游击队更是缺乏高层的政治资源,许多领导被打成叛徒。
这个时候,游击队干部越发依赖去走“群众路线”,通过向下层群众输送利益和提供庇护,来换取基层群众的支持。其实在文革中权力斗中, 各个政治势力争除了高层支持,也寻求方法动员更多的群众,就能够在向上级和对手展示实力,以求压倒对方。
这个时候,其实群众也会和各个势力谈判,例如,改善经济条件,上调工资,增加福利等条件。各个政治势力必须通向下输送利益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1974年4月,文革出身的上海代表黄涛在国家计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指责交通部要进口大平板拖车,大骂“进口就是洋奴,我们上海能生产,为什么要进口,我看外贸部就有李鸿章式的人物——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 即使交通部解释,进口是因为上海已经两次拒绝交通部的要求。但是,黄涛还是报抄王洪文和张春桥。此时的王洪文已经不是那个小偷小摸的保卫科员,而是革命的继承人,口气咄咄逼人,大义凌然,批示道,“我赞同春桥的看法:他们买了那么洋破烂,不知道洛克希德公司给了多少回扣?要彻底追查!”
其实,无非就是动了上海的利益罢了,有项目才能有财政拨款,才能为追随者提供福利回报。
凭借大寨模式一步登天的陈永贵也是如此。吴敬琏《大寨经济学》就意外的发现了1973~1974年的收入清单,其中只有40%来自于粮食,另外有40%来自于卡车的运输获利和20%的其它获利,陈永贵虽然娴熟的批判“资本主义路线”,但还是得通过这种方式秘密向农民输送利益。
在体制出现意识形态动员之后的疲态时,主义和生意、理想和现实,上层和下层以一种极端诡异而讽刺的方式交合在了一起。
不过,由于浙江游击队干部处于权力的边缘位置,体制内的资源有限,所以提供的不是直接的物质福利,而是制度庇护,一种非正式的、地方性的产权保护。
由于这是在特殊地区且非正式的产权保护,对于浙江的经济总量并没有太多作用,在1952~1976年,浙江省的人均 GDP 都远低于全国的人均 GDP,其本质上是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1966年,全国人均 GDP 是浙江人均 GDP的1.2倍,但是在1976年就达到了1.42倍,越来越穷。
但是,它却深刻改变了浙江游击地区的经济形态。
以宁波下辖的三个县在1966年到1978年的经济结构变化为例,慈溪196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比例为80. 28%,1978年降为43.9%,宁海1966年为81.58%下降为39.04%,余姚1966年68.76%,1978年为29.5%。温州也经历的类似的变化,1976年的社队企业的工业产值已经是1965年的5倍左右。
所谓社队企业其实本质是当地干部为掩护私营经济提供的挂靠服务,当地农民只要上缴一定的管理费用,就可以开办工厂。文革后期,1975~1977年,永嘉和瑞安两县生产的阀门就是华为五省的1.5倍,整个上海的产量。在之前表现突出的乐清柳市镇,则直接出现了不挂靠社队的地下工厂,1976年,当地家庭工厂的产值已经是国营企业的2倍。
群众对此也是投桃报李,在温州市高层干部被造反被揪出批斗关押之际,基层干部得到了群众的保护。 乐清偃湖公社的党委书记,就因为善待群众,屡次得到群众庇护,不仅拒绝造反派把他当做当权派批判,更在造反派冲击镇政府时,帮助其将造反派驱逐出去。有一次,红卫兵将乐清县县长抓到群众大会上批判时,当地群众在其他游击干部的动员下,竟然冲击会场将其置于自己保护之下。
其实,这可能并不只是浙江的故事,只要地方的权力结构中存在边缘群体,这种激励和故事就应该存在,比如说远在云南的褚时健。
褚时健本身就是在云南解放前入党,属于游击队出身,在征粮和土改中一直都是温和派。1958年,因为为人正直和反右专员发生矛盾,被划为“右”派。当时,褚时健拒绝为专员提供额外福利,被专门开会批斗。专员怒斥:“褚时健你这个人事科长怎么当的,专员都快饿死了!”
自此,褚时健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从革命变成反革命。不到3年,他的右派帽子被摘下,但留下了污点,给出的解释是将帽子放到人民群众手里,如果表现不好,就要重新戴回来。
不过,作为一个“右派”污点的干部,他却相对平静地渡过了文革岁月,凭借的就是所谓的“走群众路线”。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在一个糖厂做副厂长,属于边缘人物,但是并不参与任何的政治斗争,一心一意抓生产。不仅操心生产,而且花心思提高厂子工人的福利,他的夫人就认为褚时健最高明之处不在经营生产,而在于提高工人福利。在《褚时健传》中有描述:
“当时国家统一供应每人每个月1公斤肉,4两油,过去食堂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现在食堂每个星期就杀一头猪,一家人只要出5角钱,就能用浇菜的那种大铝瓢,到食堂去打上满满一瓢香喷喷的肉,这个画面在那个年代确实太刺激了。”
由于福利好,群众基础好,在开批斗会时,厂里都会传话:“我们写大字报完全是出于无奈……”“我们在前面闹革命,褚副厂长还是要在后面抓生产……”
正是因为褚时健实实在在地给当地的群众带来了福利,所以,才能靠着群众路线顺利过关。
3
1978年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得到承认。实际上,政治是保守势力和改革势力处于不断的交锋。
1981年,《人民日报》发文讨论一位养鱼能手陈志雄雇佣工人是否违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立刻表态,给广东省委任仲夷写信表示陈志雄的做法“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作出明确的规定予以制止或矫正,并且全省通报”。不过,在广东省委的力挺和保护之下,不了了之。
但是安徽就是另一幅光景。1978年,安徽小岗村几个农民的托孤协议现在被中国官方认定的最早的包产到户的地方,在中国官方改革开放的记录中,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存在,包产到户就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不然,当时很多的政策都是看省委书记的意向。在万里离开安徽之后,新任的省委书记不支持包产到户,上任之后,立刻限制。安徽再次开始包产到户,其实是在中央的改革的局势更加明朗之后了,当然这位省委书记最后也是以改革自居。
1980年邓小平侧面表态:偏远地区可以放开。但是中央开会,各个地方负责人交锋激烈。根据中国改革的元老杜润生的回忆:
“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
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认为:“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贵州省池必卿针锋相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但是,浙江非常独特。当时的浙江省委领导并不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经济还是发展了起来。
1981年,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常委袁芳烈出任温州市市委书记,省委就嘱咐他要解决“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袁芳烈一到温州就感觉是到了“敌占区”。
1982年,胡乔木在调查走私问题时,强调走私是“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的一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中的一个总要环节”,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打击面从走私扩大到了投机倒把。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温州发生了八大王被抓事件,震动整个温州,第二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2%,私营部门工业产出减少75%。当时,温州干部也对此产生了抵制,公然质疑省委的决定,还有干部写了130万字的申诉材料,把状告到了胡耀邦那里。不过,后来随着中央改革力量占上风,袁芳烈也开始转向改革,给八大王平了反,还支持了信用社的浮动汇率制改革和默许了温州的地下钱庄。
但是,这种态度转变让浙江省委很不满,于是又派了另一位党性极强的干部——董朝才去恢复当地国有经济的活力,结果发现他们的转变极其相似:打击违法犯罪经济活动,地方干部的抵制和经济萎缩,平反企业家案件,积极的支持改革。董朝才不仅支持了股份合作制企业合法化,更加支持了1984国内第一家民营“银行”——方兴钱庄。
吴晓波老师曾提到,方培林的方兴钱庄第二天就被摘牌。其实不然,当时国有银行行长确实反对说放贷是他们的管的事情,但是董朝才告诫“银行的党委书记归我管”,这个民营银行一直顽强存在了4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后来,董朝才的总结出了“人民社会主义”的理论:
“温州这些年发展很大,归根到底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后面是什么呢?是人民社会主义,人民来建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确已经达到这个目的。”
如果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区域中民营经济中发达都跟解放之前的游击队有些关系,如:“泉州和闽中游击队,冀东游击队和河北唐山还有最著名的珠江三角洲和东江游击队。”
但观察到这种独特现象的章奇和刘明兴进一步指出,重要的并不是干部出身游击队或者本地,而是其处体制内边缘化的力量,比如在浙江的临省江苏,更加支持改革的就是身处苏南的南下干部,因为他们在江苏省的权力格局中处于边缘的位置,而华中根据地出身的干部得益于历史原因,非常强势,一直在解放后的江苏省委中占主导地位,其主导的苏北地区一贯比较“左倾”,几乎是浙江的反面。
1968~1978年,在无锡、苏州等南下干部主导的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35.62%,所谓社队工业其本质就是乡镇企业的雏形。在无锡县,1978年,社队工业产值占据总产值64.85%,而在江阴和宜兴县,社队工业产业也占到了55.34%和44.80%,而全面所有制工业产值比重大幅下降最高达40%以上。苏州地区也出现相似的变化。
在文革期间,非公有制经济在浙江和江苏的表现确实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章明和刘明兴的假说。
这个时候,王石的问题就有了可能的答案,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是直接来源于历史传统,而是来自于具体的历史实践,源于地方部门在激励下的灵活变通和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5
但是这种特定历史阶段下的产权保护是有局限的,江苏和浙江起点的不同,就暗示了它的缺陷
从激励的角度上看,如果处于体制内的强势地位,官员就更倾向持国有经济,因为可以独享体制内的福利。如果稍弱,就更愿意支持集体经济,虽然要向群众分享权力, 但是集体经济形式可以确保自己在分享利益时的强势地位;如果弱势,那么就更加可能支持民营经济,因为他需要从群众得到的支持更多。
这种特定历史阶段的产权保护,其本是体制内被边缘化的权力精英向基层输送利益换取支持,其输送利益的强度和大小就去决定于自身边缘化的程度。浙江温州的私营经济和江苏的从集体经济转型而来的乡镇企业更多是反应各自在体制内的权力位置,显然江苏干部也强势得多。
新望在《苏南模式的终结》谈到:
“苏南的企业家,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们都处在权力照射范围之内,具备‘体制内’身份,不在权力光束范围内的一般社会成员则很难创业。”
其实,同样的逻辑也发生在改革初期的广东华南地区。
比如说,在吴晓波笔下极其悲情的潘宁和容声冰箱的故事,其本人也就是基层干部出身。潘宁为了规避政策风险在注册容声冰箱时就是乡镇集体企业,潘宁就是在做强做大之后,希望能明晰产权时,当地干部一直含糊推诿,最终酿成潘宁的出走,之后更牵扯出顾雏军的冤案,直到2018年高法为其平反,但心有不甘的顾雏军还是坚持赔偿,余波至今未平。
所以,最早期的乡镇企业就是“小全民”的乡镇国有经济。不过,因为产权不清导致企业经营不善后,连锁引发乡镇的财政困境后,这时他们又迅速被当成包袱甩了出去,这就是20世纪末对于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
当时苏南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口号,例如横泾镇就下发了,“鼓励XX干部从事私营经济的意见”、“关于XX干部带头创业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意见”,简称“双带”,当地调侃政策说,“让你富,你不得不富”。
这次改制是明晰产权的必须,但是由于经营者属于体制内的身份,和权力纠缠不清,其基层员工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尊重,改革总有牺牲,但是有些人付出了过多的牺牲,这种社会隐痛一直是企业家的软肋。
更值得深思的是,实改制之后的江苏经济最大的特点并不是民营经济的崛起,而是招商引资的热潮,特别是对于外资和台资,其中的代表是苏州工业园区和昆山经济。
原本以为产权改制完成之后,在地方“锦标赛”模式的激励下,地方干部就会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其实不然,地方干部的策略有很多,扶植民营企业是辛苦活,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失败的风险很大,加上任期限制,很有可能能吃力不讨好。
相比之下,招商引资就更方便,特别是外资。相比于民营资本,外资的科技含量更高,而且一些实力雄厚的公司的入驻,往往能带动上下游更多的企业进入地方,不但解决就业,而且可以带动所谓的产业升级,可谓冠冕堂皇。新望分享过一个荒唐的故事:
“某台商出国从机场回来后,当晚没有到家,太太很着急,于是找到了当地的招商引资办公室,办公室人员连夜发动大家找人,最后发现这位台商去了‘包二奶’家。如何向家里的太太交代,引资办的人说,你老公工作繁忙,从机场驾车回来的路上实在太困,就把车子停在路边睡着了。”
招商引资本是一个正常现象,但黄亚生就观察到一个负面现象,乡镇企业改制之后,不少江苏省的民资企业开始伪装 FDI 的方式,获取优待和产权保护。其本质说明,制度激励之下,还是有产权歧视。
例如,江苏两位因招商引资出名的两位能吏——季建业和仇和,都因为牵扯入权力的寻租而锒铛入狱,仇和还曾留下过“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这一名句,为民间和媒体传唱。这就是由于没有清晰的产权改革,改革沦为自我寻租的工具——以改革之名行寻租之实。
6
最开始从事民营经济的企业家其实都源于非体制内的边缘群体,冒险、勤奋和机遇让他们在体制的缝隙中发展壮大,这不仅满足了他们最初生存的愿望,也成为阶层上升的渠道,这也是中国的梦想之所在。
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根据贾瑞雪和兰小欢通过研究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没有背景的平凡群众更愿意经商,但90年代后,官员子女从商的比例大大增加,并且很快超过普通人。还有一个更值得深究的现象是国家财政占 GDP 比重的变化,正是在1993年后,财政占 GDP比重由降转升的时候,普通人成为企业家的意愿降低,而官员子女持续上升。
来源:贾瑞雪和兰小红的研究(见尾注5)
不仅如此,William Parish和Ethan Michelson曾经利用1988年的抽样数据研究发现,在农村地区,不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干部家庭的收入高出其他家庭40%的水平,其收入差距并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升高而降低。
著名的社会学家周雪光利用1993~1994年全国20个城市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的收入始终居高不下,虽然教育的汇报确实是在增加,虽然仍然比不上政府官员的身份。最让人长叹的是吴晓刚和谢宇的研究。他们比较了1987年和1996年的数据发现,市场部门的收入是比政府部门的收入高出26%,而且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在市场的收入比在政府要高,但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改变的不仅仅是市场而是两种人,一种是体制内边缘化的群体被迫入进市场,另一种则是体制内的精英发现机会,来此寻宝。企业家已经不是那么草根了。
互联网行业是中国最市场化的行业,但最出色的年轻人王兴、程维和张一鸣,至少都是出自公务员家庭。有时候媒体感慨没有新故事,是不是反思一下,新人何在?
前一段时间,由于去杠杆、贸易战、税收调整和股权质押等负面消息接连不断,民营企业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想太多,国家连忙出面安抚才稳住人心。
其实,中国经济在新旧转换之间,宏观形势的收紧不可避免,有一些民营企业的死亡,很大程度上有自己的原因,加杠杆,炒房产、疯狂负债,不专心提高产品竞争力,死亡本就是一个市场淘汰的过程,没有什么好可惜的。曹德旺在接受新京报媒体采访时,就直言这次民营企业的困境主要原因在自己:
“短贷长投是这次民企困境爆炸的导火索,但根本症结在企业家的“头(脑)......民企跟银行签订一年的贷款合同,拿着这种短期融资去做长期投资,希望能够赚快钱。但这无异于火中取栗,到炭火中取栗子,肯定要被烫到手。等银行贷款到期,企业放出去的投资的钱收不回来,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出问题的企业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状态。很少有企业的老板意识到短贷不能拿去做长投。企业家你把企业的股票拿去抵押,抵押了做什么?拿去投资,知道投资有风险吗?企业现在崩盘了,政府拿钱去救,这公平吗?”
其实,真正应该在意的应该是呵护企业家精神,它只能在宽容、平等和自由的气氛中成长。中国经济奇迹从来不在存量,而在增量。不在过去的成就和现在的困难,而在未来的可能性。
回顾中国经济奇迹,总结起来两句话:给市场以空间,给边缘人以机会。
百万用户都在读
金融委专题会议再做五大定调!副总理刘鹤主持,稳市场规则成熟后立即推出,股市汇市融资都有涉及
“浙江帮”,资本市场最豪华朋友圈:金科文化3年做局,大佬步步惊心!
孙立平: 当前最急迫的三个问题——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百姓的希望感
违约进入下半场:从民营企业接盘到居民破产!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由FMBA历届校友推荐的文章集锦,版权属于原作者

关注公众号:拾黑(shiheibook)了解更多
[广告]赞助链接:
四季很好,只要有你,文娱排行榜:https://www.yaopaiming.com/
让资讯触达的更精准有趣:https://www.0xu.cn/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
关注网络尖刀微信公众号随时掌握互联网精彩
- 1 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 7904654
- 2 2262年两个春节只放1次假 7808570
- 3 解放军实现3公里外激光远程排弹 7712771
- 4 全岛封关 去海南旅游购物有啥利好 7618661
- 5 广西发现稀有血型“恐龙血” 7521842
- 6 海南封关首日居民排长队买榴莲 7428119
- 7 国际航班外籍男子辱骂骚扰中国女生 7330705
- 8 王毅分别同柬埔寨、泰国外长通电话 7233991
- 9 女孩穿“光腿神器”进急诊 医生提醒 7140081
- 10 中方回应日本拟用雷达监视中国航母 7043580














 FMBA
FMBA